|
版权所有© 中外文学研究课题组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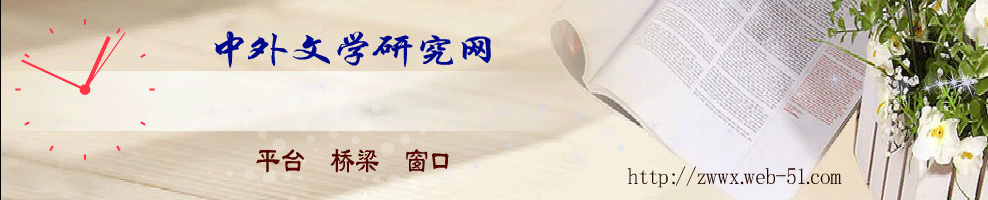
宋虎堂
(西北师范大学 文学院, 甘肃 兰州 730070)
摘 要:《窄门》是法国作家安德烈•纪德创作成熟时期的作品。要挖掘隐藏在《窄门》字面意义背后更加深层的意图,就必须从该作品的艺术表达方式入手,这种方式就是来源于《圣经》的一种隐喻的整体表达方式。《窄门》是一个由《圣经》的象征符码“伊甸园——天堂”和“窄门——十字架”组成的双重隐喻世界。它们之间环环相扣,层层深入,全面而深刻地向人们展示了作品主题的精神实质和价值意义:寻找精神家园。
关键词:“伊甸园——天堂”;“窄门——十字架”;隐喻;精神家园
20世纪法国作家安德烈•纪德是一个颇受争议的作家。《窄门》(1909)是纪德创作成熟时期所发表的一部小说,它讲述了阿莉莎和热罗姆的爱情故事。女主人公阿莉莎恪守福音书中的训示,追求一种柏拉图式的精神恋爱,一直坚信自己能到达通往天堂的窄门,然而通往天堂的窄门只能一个人通过,容不下两个人。最后不惜为宗教而牺牲了自己的爱情和生命。
由于纪德的文学观与宗教观总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所以,我们必须从纪德接受基督教的根源——《圣经》出发,去分析《窄门》。以往的一些评论往往仅从《窄门》的题目和题材与《圣经》的关系入手,认为《窄门》是纪德对限制人们行动,扼杀人们正常情感的福音书以及基督教的批判。如果从关注“人”、“人性”的角度来说,纪德的确对福音书中那些扼杀人们天性的训示作了一次深刻的反思和批判,但这种理解只是从字面意义上得出的片面结论。而要挖掘隐藏在字面背后作家更加深层的意图时,我们还必须从作者的表达方式入手,这种方式就是来源于《圣经》的一种隐喻的整体表达方式。
“隐喻,连同与其相关的比喻、讽喻、象征、寓言等,是《圣经》中举目可见的文学想象,基本特征在于‘意在言外、言此及彼’。它不仅是圣经作者最常使用的修辞手段,也是普遍存在于希伯来——基督教文化中的重要思维模式。”①在隐喻以及类似的非字面语言中,隐含意义乃是最主要的构成因素。这些隐喻的价值就在于:时常能够、有时甚至出乎意料地以不同寻常的方式表达和传递出巨大的情感内涵和生命体验,常常能够真实再现场景、表现生动意象。弗莱在《伟大的代码》一书中用“隐喻”一词概括了圣经意象的整体化原则,他说:“隐喻也许并不是圣经语言的一种偶然性的装饰,而是圣经语言的一种思想控制模式。”①
这种整体的隐喻既是一种把握世界的思维方式,又是一种认识世界的修辞艺术。隐喻发端于主体以自身的生命形式去体认、观察和命名自然世界的活动中。
一、“伊甸园——天堂”的隐喻
自人类被上帝逐出伊甸园的那天起,在现实生活中的人类对于重返伊甸园的梦想就从来没有停止过。作为西方文学三大源头之一的《圣经》中的伊甸园,无疑是《圣经》中神话和传说完美结合的产物,已经成为人类美好家园的普通意象,成了人类原始生活与情感完美无暇的一种象征。纪德在《窄门》的开端就为我们描绘了一幅现代“伊甸园”的美丽画面:一到风和日丽的季节,我们就去比科兰舅舅家,比科兰家的房子坐落在一个大花园里,花园是长方形的,四周有围墙,与许多诺曼底花园相似。在房屋前面有一块被绿阴覆盖的、相当大的草坪,草坪周围有一条沙石的小路。在花园的西面,一条开满鲜花的小路从朝南的果树架前经过,浓密的葡萄牙月桂和几株树使小径免受海风的蹂躏。另一条小径沿着北面的围墙延伸,消失在树丛中。一到美丽的夏日黄昏,他们吃过晚饭后便来到这个花园,从西面的台阶上,去欣赏高原的庄稼,而在天边,小村的教堂隐约可见。热罗姆和阿莉莎有一段时期就生活在这个大花园中,在这宁静的田园风光中,人与自然处于一种和谐的自然环境中,犹如生活在一个伊甸园中。虽然不是《圣经》中所描述的伊甸园,但纪德通过他们生活的大花园,一方面,给男女主人公创建了一个现代的“伊甸园”,这其实也是纪德为自己建造的伊甸园;另一方面,这个“伊甸园”又是一种精神意识的乐园,目的就是回归已经失去的“伊甸园”。这是一个新的伊甸园,
伊甸园是人类始祖亚当和夏娃最初居住的乐园。复归伊甸园,是人类怀旧与求新双重心理的情结。如何复归伊甸园?不仅要看时代所提供的可能性,而且要看个体的心理素质和心理结构方式。“伊甸园”在纪德的《窄门》中表现出两种意义:一是回归人类完美生活的乐园;一是指向人类心灵深处的缺失。这两层意义,恰如弗莱在《伟大的代码》中所说的那样,伊甸园的隐喻将自然分为两个层次:“低的层次就是上帝对挪亚的喻示中所预言的,一个被人类主宰与剥夺的自然;高的层次则是上帝在伊甸园中对亚当的早期训示中所说的,人类在本质上所从属的自然,而伊甸园故事则预示了人类回到这个高层次,得到拯救。”①纪德作为一个始终热衷于现实生活写作的作家,强调和拯救的是精神的自然,对精神的伊甸园的追寻与重建的希求充满了《窄门》的思想细胞。
纪德将自己作品中的人物放置在自我构建的“伊甸园”中,希望热罗姆和阿莉莎在其中快乐地生活相爱。如果我们把热罗姆比作亚当,阿莉莎比作夏娃的话,他们俩都在上帝的旨意下追求一种“伊甸园”式的纯洁而完美的爱情。这种幸福的爱情只能在宗教信仰中获得,因为在阿莉莎眼中,此生的快乐远远不是生命本身所拥有的,而是我们向更高的生活境界追求中的一种恐惧;同样,此生的痛苦也不是生命本身所拥有的,而是在追求一种理想境界时由恐惧所引起的一种自我折磨方式。可以说,热罗姆和阿莉莎在追求“伊甸园”式的爱情中,逐渐生活在两个极点:一个生活在现实的“伊甸园”中,虽然也信奉上帝,但更侧重对德行的追求;而另一个则完全生活在《圣经》的“伊甸园”中,追求一种彼岸世界的爱情。
在基督教神学的结构中,伊甸园处于“地狱—人间—伊甸园—天堂”的这个体系中。这四个层次不仅成为一种空间或时间上的概念,而且成为了人们精神上的一种永恒的、向上的追求。在《窄门》中,纪德通过阿莉莎与热罗姆那种虔诚的爱情,一直试图为自己和他人寻找到一个无忧无虑,快乐生活的乐园。如果从艺术的角度来说,那就是回归自然,回归本我,更重要的是回归精神的乐园,回到母性的怀抱。在一定意义上,纪德与表姐玛德莱娜之间那种复杂的关系就是纪德与母亲之间的关系在《窄门》中的延续。如果从生活的角度,更确切地说,纪德心目中所追寻的“伊甸园”就是玛德莱娜。纪德爱玛德莱娜最主要的原因在于玛德莱娜能给他那烦躁不安的心灵带来一些安慰和平衡。母亲严厉的清教教育,使纪德不顾一切地寻找属于自己的生活。然而,在寻找的过程中,他在茫然中需要一种“爱”来指点方向,而玛德莱娜恰好充当了纪德寻找“伊甸园”的向导。玛德莱娜使纪德有了释放自己激情的机会,也使他漂泊的灵魂有了一个停泊的港湾。玛德莱娜的爱拯救了纪德,也碰撞出了创作《窄门》的热情,这种“爱”给了纪德无穷的精神动力。因此,如果说纪德在现代为自己和他人指出了回归“伊甸园”的道路的话,那么阿莉莎则为人们指出了一条通向“天堂”的道路,虽然达到天堂的道路极其艰难。
在阿莉莎身上,“伊甸园—天堂”有时是重合的,它们都是阿莉莎内心世界虔诚信仰地一种双重反映。阿莉莎为什么那样地虔诚?主要来自于《圣经》对她的引导,对于她来说,圣洁并不是一种个人的选择,而是一种职责。阿莉莎在一段时间里只读《圣经》和《榜样》(即《基督耶稣的榜样》,用拉丁文写成的经书),曾几何时,她怀着孩童般的热烈信仰,用天使般的声音向上帝呼唤:“上帝呀……我的一切,我知道,不是来自热罗姆,而是来自于您。可为什么您要将他的形象处处放在您与我之间呢?”“我清楚地感觉到,我根据自己的忧郁感觉到:我心中的牺牲并未完成。上帝啊,让我明白,他曾带给我的那种喜悦,其实是您赐给的呀。”①然而,阿莉莎的爱情也不完全是上帝的恩赐,而是只有与热罗姆相爱才能真正地热爱上帝。如果上帝的旨意要将热罗姆赐予阿莉莎,阿莉莎就会把自己的心献给上帝,随着上帝回到她所向往的“天堂”。自从人类被逐出乐园后,上帝为了让人类重新回到乐园,为人类设置了两条救赎的目标:一是现实的幸福,二是在天堂的永恒的幸福。现实的幸福是以天堂来世的幸福为依托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阿莉莎心中只有拥有上帝,才能获得来世的幸福。她必须达到对现世事物的超越,完成肉体和灵魂的真正统一,才能实现永恒的幸福。《圣经》是指明阿莉莎爱情的一座灯塔,上帝所在的天堂才是她向往的理想胜地。
在走向天堂的过程中,阿莉莎的内心世界是很矛盾的。阿莉莎的矛盾来自与热罗姆的爱情追求中,一方面,阿莉莎的确爱着热罗姆,但同时她更加爱上帝,上帝所在的天堂是她生命的归宿;另一方面,在上帝和热罗姆之间进行选择是一件痛苦的生命体验,舍弃热罗姆是她不愿意的事情,而舍弃上帝就犹如失去生命一样,阿莉莎只能把自己的生命献于上帝来化解这种矛盾状态。同时,阿莉莎的矛盾也来自与上帝的对话和交流之中:“啊,上帝,有谁的心灵比他更能配的上您,难道他生来不是为了得到比对我的爱情更美好的东西吗?如果他在我身上停歇,我还会这样爱他吗?那一切有可能变得壮烈的东西,如果沉溺于幸福中会变得多么狭隘!……”①最后,阿莉莎以“神的法则”代替了“人的法则”,进入了天堂的“窄门”。阿莉莎的宗教感情与《圣经》的博爱的宗教关怀有了很大的距离,“苦行”变成了她宗教信仰中的唯一有效的方式,以至有的批评家认为,她的信仰与其说是新教,不如说是冉森教(冉森教是17——18世纪的教派,根据冉森的著作《奥古斯丁》发展而成,崇尚严格的伦理教条和禁欲主义)。
阿莉莎的爱情困境是纪德本人曾经深陷的情感困境,流露出纪德心底的宗教感情,是纪德对宗教神圣的一首凄美的赞歌。纪德通过阿莉莎所要表达的是一种在现实的自我和现实的生活中,此岸世界/彼岸世界、有限/无限、人性/神性的一种统一。阿莉莎在上帝面前的无法接近,不是彼岸世界的无限性,而是此岸世界的无限性,在有限的生命和有限的自我之中。
二、“窄门——十字架”的隐喻
“也许可以说,没有隐喻,没有喻词和表达,就不可能有对存在的真正思考,就不可能发现尚未言说的意义,就不可能把存在间某种内在的普遍的联系揭示出来。”②与“伊甸园——天堂”的隐喻紧密相连的是“窄门——十字架”的隐喻。纪德以“窄门”作为作品的题目,蕴涵着深刻的宗教意义。“窄门”一词出自于《圣经•路加福音》的第13章第24节耶稣对众人说的话——“你们要努力进入窄门。”基督教认为,通往地狱的门是宽大的,而通往天国的门则是窄小的。所以,人们只有克制自己的情欲,才能在死后通过窄门而获得永生。阿莉莎的“窄门”情结其实是纪德内心体验的需要,而且深深地扎根在纪德的心灵中。
我们对“窄门”意义的理解必须联系作品中“十字架”。虽然作品的题目是“窄门”,但阿莉莎追求过程的重心却在“十字架”上。“十字架”是作品中出现过几次的一种象征符码。在作品后面,热罗姆发现,阿莉莎经常在脖子里挂着一枚紫晶做的,旧的小十字架,而这个十字架则是热罗姆赠送给阿莉莎的纪念品,同时,这个十字架也是热罗姆的母亲送给他做纪念品的。在《圣经》中,当耶酥基督被钉上十字架时,十字架已不再是残酷的刑具,而是耶稣基督“爱”的彰显。我们在《圣经》中体会到的十字架,首先说明耶稣给门徒的唯一命令就是“爱”;其次说明耶稣自己就是在十字架上活出了爱。十字架的“十”作为人类心象模式的客观对应物,它是基督教文化中的元结构,体现着对立统一的思维构成原则。阿莉莎在《圣经》的影响和熏陶下,就是以这样的思维方式理解她和热罗姆的爱情的。十字架的宗教,一方面说明天国之纯洁与人世水火之罪恶,同时也表现出上帝对世人的宽宏、怜悯;另一方面也形象地表达出人之终极关切与实际存在之间的有机联系及内在矛盾。不容阿莉莎所走的窄门之路,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十字架之路,既在十字架上死而复生的道路。因为,自从亚当、夏娃偷吃禁果以来,人类就陷入深深的原罪中不能自拔。上帝遂道成肉身,以在十字架上的死,为人类“献了一次永远的赎罪祭”(《希伯来书》,10:12),随后复活。上帝为人类建立了一种为自己赎罪的模式和榜样,即走背负“十字架”的“窄门”之路。阿莉莎要想在上帝所在的天国享受彼岸世界的幸福,她就必须在现世中背负起信仰的“十字架”,走向复活和永恒。“人要想达到永恒,惟一的出路就是永恒的追求,在追求中毫不迟疑地背负起在与异性的对抗与融合中萌生的全部幸福和痛苦、美丽与丑陋、欢乐与苦难的十字架。如此,人才能与‘用真理那活生生的结构构建起来世界和拱在我们头上的天堂遥相呼应,浑然一体’”。①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阿莉莎走的又是一条复活的道路,她心中时时有上帝,在现实生活中上帝缺席的处境中走向自我担当,在某种程度上是把自己当作实验品来代替上帝,在《圣经》的指引下来重新阐释人类生存的基本信念。基督教的“复活”有两层的含义:一是耶稣基督在被钉十字架后的复活,二是世上的罪人得到基督拯救而复活。纪德将“复活”的意义赋予阿莉莎。阿莉莎身上所体现出来的品质是二元性(宗教/道德)的,其身上的基督性是以个体的生存境遇为基础的,是一种个体自律的救赎价值形态。
基督教《圣经》是建立在上帝与人相互信守的契约文化的核心意识之上,这个“约”的文化信息背后潜沉着的正是那个无所不能的十字架。一方面,人是有自由意志的主体存在,是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人的超动物性使人类超越自身,将自身的主观精神运用到认识自我与上帝、自我与现实世界的思维信仰活动中。另一方面,人类对自然的强行索取在历史的演进中又造成了历史与人伦的二元悖论,使人类背负痛苦和不幸。然而,人作为世界中的存在,必须有一种信仰来支撑自我的价值追求体系,不得不去处理人与上帝、人与社会的关系。一方面,整个世界是上帝写的一本大书,上帝在一定程度上默认了人类行为的合理性存在,另一方面又将人的幸与不幸的双重状态转化为超越人性的合理性要求之上,在人向人性和神性的张力和超越中,“窄门——十字架”将人与社会、理想与现实、有限与无限等的二元对立转化为一种互补性的约定。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阿莉莎的“十字架”信仰就是她与上帝的一种“约”,这个“约”不仅仅是实物“十字架”的语义表达,更是阿莉莎心中“十字架”的意识思维结构,这两方面“表面上看来由耶稣殉难演化而来的‘十’字架根本上体现了基督教《圣经》的核心精神,成为其强大生命力的根株,并泛化在西方文化土壤之中,为西方民族所普遍拥有,成为规范后世并产生稳定性影响的文化基因。”①
基督教作为人类精神的一种信仰,其根本的价值和旨意在于超越,这种超越性首先表现在上帝的那种超自然、超越人类的象征力量上,表现在彼岸天国对现实世界的许诺以及使人在上帝的调节下从现实中解脱和超拔出来的一种神奇力量。阿莉莎在现实中追求的是“窄门——十字架”的信仰,以达到对基督的绝对肯定,并在与上帝的对话中实现个体最自身有限性和不完善性的超越和转换,最终完成人与上帝的统一。阿莉莎身上所带的“十字架”所展现的是一种时空纵横、对立统一、两极相通的信仰图景。它的一端预示着上帝永恒、无限、绝对、完善等终极意义,另一端则反映出一种人之历史的相对性和有限作为。阿莉莎的死亡将这不可企及的两极打通,因为基督的十字架既意味着永恒对人们心灵世界的召唤,又代表着人性之完美的一种典范。因此,“十字架”所带给阿莉莎的生活真理是在信奉基督的基础上,去超越自我,追求永恒,使自己的爱情在“十字架”意义上达到完善。同时,阿莉莎不仅自己以身作则,而且将这种虔诚的信仰传达给周围的其他人。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纪德“窄门——十字架”的信仰所要表达的是一种人性的“复活”和自我的超越,是用生命和爱换来的一种永恒的精神境界。
总的来看,纪德是怀着一种强烈的激情和深刻的心灵共振去描写阿莉莎极其虔诚的美德和向往。“伊甸园——天堂”和“窄门——十字架”的象征符码不仅突破了《圣经》中的具体含义,更是在《窄门》中构成了重新被纪德思维结构书写的《圣经》的象征符码。纪德关心的不再是故事的有趣和复杂,而是这些象征符码的审美形式和审美意义。纪德的职责也不在于怎样去修饰故事,而在于揭示这些隐含和显现的象征符码,揭示这些象征符码内所隐藏的观念和真理。因此,这些象征符码就是构成纪德《圣经》情结的内涵所在。纪德对《圣经》中这些象征符码的重温和重解以及审美性的关注,不仅是纪德恢复失去人间“伊甸园”、“天堂”的一条途径,而且表露出纪德在圣洁之爱中对伊甸乐园的怀旧情愫。
三、寻找精神家园的“浪子”
无论是从“伊甸园”到“天堂”,还是背负“十字架”进入“窄门”的历程;无论是最初纪德为热罗姆和阿莉莎创建的“伊甸园”,还是最后阿莉莎灵魂进入的“天堂”,这些象征符码所构成的思维历程,其最终的指向都是纪德和喜爱他的读者的心灵世界和灵魂归宿。那么纪德通过热罗姆和阿莉莎的爱情故事,所要表达的精神实质和价值意义是什么呢?答案是:追求—寻找精神家园。
19世纪后期随着西方工业文明的发达,带给人们丰富物质的同时,也带给人们精神家园的缺失。在18世纪理性精神基础上建立的国家,曾经以理性和自制为特征的社会制度和道德规范逐渐成为限制个体自由的公共伦理,已不适应现代人的生活状况,而个体的差异性感受和价值偏好则成为这种公共伦理极力压制的对象。自西方人从几个世纪前就开始反对反抗基督教神学的黑暗统治,争取人权和个性解放,然而,在人们最大限度地享受着物质文明的时候,却又渐渐地感到了精神的空虚和孤独,感到了灵魂无所归依的痛苦。同时,世纪之交,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剧烈角逐,给人们的心灵带来了强烈的震撼。传统文化一向讲究秩序,而现代文化弘扬自我,注重情感,它们的不平衡发展往往给人们带来精神的困惑,每个人的心理成了这两种文化角逐的战场,反映在社会生活中,就是人们感到理想遥不可及,前途迷茫,退亦忧,进亦忧,即使作出了很大的牺牲,也不能将传统与现代统一起来。“上帝死了!”(尼采语)和“上帝不存在是一个极端尴尬的事情”(萨特语)的感慨是对西方人精神家园缺失的无奈哀叹。的确,人们不能没有对高尚精神追求的终极关怀,也不能没有一个灵魂的港湾和精神的栖息地。西方基督教宣扬对上帝和天国的信仰,使西方人在多少个世纪的漫长岁月中有一个人生的最高目标,他们相信只有恪守基督教人向善的信条、用高尚的道德观念严格地约束自己、无条件地将自己的身心献给上帝,就能救赎自己的灵魂,从而重返无比美好的天国世界。但是在新的世纪,上帝在人们心目中的缺席并不能阻止人们在文学作品中去重塑上帝和自我,并希望寻找到自我的精神家园。生活在现实中的纪德也不例外,在对传统道德规范的质疑中,他开始了寻找自我和追求自由的精神实践。
寻找“精神家园”可以说是中外文学的一条永恒的主线。寻找“精神家园”寻找的是生命的意义和依据,也是围绕人的生存来展开的。纪德以自己独特的生命审美体验来表达自己内心的冲突、虚无感和对意义的焦虑,同时也以隐喻的艺术方式使这些心灵体验上升到了生命哲学的层次,顽强地寻找生存在形而上层面上的意义以及行动的依据,执著地寻找精神家园。早在1893年5月出版的《乌连之旅》(又译《于里安游记》)中,纪德就采用虚构的方式向我们展示了一次寻找精神家园的旅程。在作品的序曲中,主人公于里安就开门见山地指出了这次旅行的目的和缘由,“当苦读、沉思和神学遐想结束之后,我从那晚上起一直在燃烧的灵魂,既孤独又忠诚,……我在灵魂轮回的峡谷中徘徊探索。……我们过于年轻的灵魂将寻找自己的勇气,”①去追求未知的命运。这是一次心灵之旅,是在精神世界里的一首《神曲》,在航海中这些素不相识的年轻人看到了那些美丽的海上浮岛以及岛上的人鱼、陷入迷狂状态中的舞者、醉心于抽象思考的爱丽丝等等,他们都在执著地想象前面一定有美好的未来在等待他们,虽然最后他们一无所获,但他们在思想上进行了一次革命性的洗礼,展现了一种超越现实生活的心境。而1907年出版的《浪子回头》,直接引用《圣经•路加福音》的典故,纪德在作品中通过浪子与父母和弟弟的谈话,似乎去重新造就一个新的浪子,这显然和福音书的教义是相悖的。纪德在作品的前言中写道:“我任由我的双重感兴处在散乱含混的状态,并不想表彰任何神明对于我的胜利——也不想表彰我自己的胜利。然而读者问我要虔诚,也许在我的书中不至于找不到:在那儿,像一个施主在图角上,我跪着,学浪子的模样,同时也像他一样地一边含笑,一边挂一脸眼泪”。②纪德的用意并不仅仅在于反叛福音书和记述浪子的归来,而更重要的是表达一种精神家园的寻求。浪子回来了,回归的目的是为了回归自我。浪子身体的回归只是一种表面形式,他的心灵和精神还在流浪。现在有论者把纪德和阿莉莎看成浪子,在尘世中为生存而探索、追寻。其实,无论是离家出走的浪子还是一心想进入窄门的阿莉莎,纪德和他创作的人物已不是一个物质实体,而是一种精神的化身。阿莉莎在虚无的追求中创造自我,解构、结构自我,在追求中重塑自我,不仅代表了一种生活方式,更重要的是代表了人们的一种价值趋向和思维方式。
我们再回头看看西方文学中那些经典的作品,自从古希腊罗马时代到20世纪,人们一直在寻找自己的精神家园,每一部经典的作品都给我们展示着寻找乐园和解读生活奥秘的方式,可以说都是一种寻找精神家园的艺术化表达和生活审美经验的传达。古希腊罗马人是倾听着神话和英雄传说,在丰富的想象中寻找自己的精神家园;《奥德赛》中奥德修斯的回家,不仅是回到作为实体的家园与妻儿团聚,更是为了寻找心中的精神家园。而在《神曲》中,维吉尔、贝雅特丽采带领但丁寻找的精神家园是“人间天堂”。文艺复兴时期那些激进的人文主义者曾返回古希腊罗马文化中寻找精神家园;在18世纪,歌德的《浮士德》返回古典的瓦尔普吉斯之夜“神话之国来求生”。一旦触到古希腊神话的土,浮士德就从沉睡中“焕发出新的精神”,在神话思维的艺术虚构时空中,浮士德的人生经历是这种神话时空化入社会时空的一种艺术表现。19世纪的雨果、狄更斯、哈代通过创作为社会的和谐寻求出路;而托尔斯泰在世纪至交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艰难地宣传着自己“善与爱”的思想,“托尔斯泰主义”成了整个俄罗斯乃至世界人民的心灵家园。马克•吐温的小说则成了孩子们寻找童年乐趣的精神乐园。到了20世纪,卡夫卡在孤独地寻找着自己的“城堡”,普鲁斯特在《追忆逝水年华》中寻找往昔的美好时光,而海明威则在顽强地寻求和实践着他的“男人哲学”,这样的例子举不胜举,鲜明而深刻地反映了人们寻找精神家园的心路历程。所以说,寻找精神家园不仅是纪德所追求的,而是西方作家和信仰上帝的子民,甚至几乎是生活在现世中所有人追求的“大地食粮”和心理慰藉。
①梁工《圣经叙事艺术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年7月第1版,第323—324页。
①[加]诺思洛普·弗莱著:《伟大的代码——圣经与文学》,郝振益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1版.第82页。
①[加]诺思洛普·弗莱《伟大的代码——圣经与文学》,郝振益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1月第1版,第182页.
①纪德《纪德文集·窄门》(二),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5月第1版,第111页。
①纪德《纪德文集·窄门》(二),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5月第1版,第108页。
②耿占春《改变世界与改变语言》,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12月第1版,第139页。
①梁工《圣经与欧美作家作品》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0年11月第1版,第221页。
①曹祖平《十字架——基督教隐结构猜想》,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5期,第72页。
①纪德《纪德文集·乌连之旅》(二),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5月第1版,第3页。
②纪德《纪德文集·浪子回头》(一),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5月第1版,第428页。
本文转载于《圣经文学研究》第二辑,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9月
 最新评论
最新评论|
版权所有© 中外文学研究课题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