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版权所有© 中外文学研究课题组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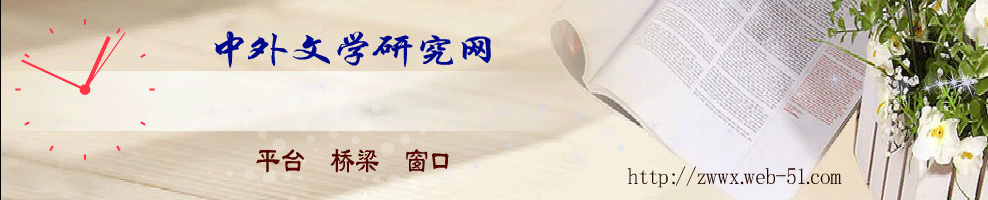
现实主义文学的生命力——新世纪中短篇小说的一个动向
张晓琴
新世纪以来,我们发现现实主义文学正悄悄地回归人们的阅读视野。从1980年代中期开始,各种文学实验思潮一浪接着一浪。进入90年代以后,这种文学实验思潮发展到极致,在令人眼花缭乱之后,人们发现真正具有持久阅读价值的仍然是那些关注现实、极富现实主义文学意义的作品,本文拟以中短篇小说为例,探讨现实主义小说在新世纪以来的新发展。在第三届、第四届鲁迅文学奖的获奖作品和入围作品中,现实主义文学作品占了相当的比例。这些作品或者是典型的现实主义手法,如《上边》、《大老郑的女人》、《松鸦为什么叫》、《玉米》、《世界上所有的夜晚》,或者是极富现实主义意味,如《黑猪毛,白猪毛》、《发廊情话》、《驮水的日子》、《歇马山庄的两个女人》、《喊山》,等等。这些小说标志了一种新的阅读期待,也说明新世纪以来当代文学对形式的过度探索正逐步走向弱化。从世界文学的发展动向来看,
说明小说回归传统的诸种可能性。作为一种创作方法,现实主义自古就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作为艺术参与社会生活的一种途径,现实主义手法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18 世纪,近代意义上的小说兴起之
时,笛福“似乎是我们的作家中第一个使其全部事件的叙述具体化到如同发生在一个实际存在的真实环境中的作家”。①“详尽的生活观”作为小说的独特特点得以确认,而“小说赖以体现其详尽的生活观的叙事方法,可以称之为形式现实主义”。②小说作为“人类经验的充分的、真实的记录”③被笛福和理查生的创作实践所证实。他们比以往作家对形式现实主义给予了更完整得多的运用。到了
19世纪,小说的“详尽的生活观”发展到极致。巴尔扎克认为:“只要严格摹写现实,一个作家可以成为或多或少忠实的、或多或少成功的、耐心的或勇敢的描绘人类典型的画家、讲述私生活戏剧的人、社会设备的考古学家、职业名册的编篡者、善恶的登记员。”④他还说:“法国社会将要做历史家,我只能当它的书记,编制恶习和德行的清单、搜集情欲的主要事实、刻画性格、选择社会上主要事件、
结合几个性质相同的性格的特点揉成典型人物,这样我也许可以写出许多历史家忘记了写的那部历史,就是说风俗史。”⑤ 19世纪现实主义文学发展到了新的高峰,产生了一批永载史册的巨匠和辉煌著作,成为后世珍贵的文学遗产,也成为20世纪中国文学的重要精神资源。干预生活曾经是我国几代作家的追求。20世纪前期,作为匕首和投枪的文学曾经发挥过重大的作用。当现代性的意识渗透进人
们的思维时,现代人的冷漠与孤独也成为现代社会的传染病。西方现代派文学深受现代社会传染病的影响,人们的灵魂孤独、寂寞、冷淡,在心灵的沙漠中飘荡。当我们共鸣于《等待戈多》的无奈与无辜时,当我们重压于《城堡》的怪圈与无助时,当我们震惊于《秃头歌女》中夫妻的陌生时,我们的生活也远离了温馨与甜美。当现代生活重重地压在现代人的心灵之上时,虚构的、玄想的文学开始大行其道。现代人在现代病面前无计可施。巴尔加斯·略萨说:“想象力为我们在有限制的现实和无节制的欲望之间不可避免地离异产生出一种灵敏的缓冲剂,即虚构。”⑥在20世纪文学的发展中,现代派的文学实践虽然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传统现实主义仍具有强大的生命力。面对现代派文学的新奇试验
与开拓,我们在最初的振奋与惊讶之后,更多地感受到肖伯纳、罗曼·罗兰、肖洛霍夫、帕斯捷尔纳克、高尔斯华绥、托马斯·曼、海明威等作家的魅力。这既是思想的魅力,也是艺术的魅力。我们看到一种穿透力,透过历史的烟云在向我们逼近。荒诞派戏剧的巨擘贝克特晚年感到写作的路子越来越窄,感到自己的写作只是同义重复。贝克特的感喟从一个方面反映了现代派文学试验的局限。当代文学经过20多年的文学实验之后,文坛逐渐从浮躁的喧嚣中沉寂下来。沉寂不是退步,而是为前进积蓄力量。新世纪以来现实主义文学取得了相当的成就。纵观这些默默的耕耘者,新的文学方法的探索并没有淡出他们的文学视野,他们仍在坚持用文学再现现实、表现现实,这是现实主义文学的生命线。
从新世纪以来中短篇小说的选题看,这个阶段的创作反映了社会生活的多个侧面,反映矿难的有《世界上所有的夜晚》、《喊山》、《黑口》、《在丰镇的大街上嚎哭》、《黑雪球》; 反映教育界黑暗面的有《怕羞的木头》、《我们的成长》、《我们能够拯救谁》、《奸细》、《掐尖麽尖》;反映三农问题的有《落果》、《蚯蚓》、《野炊图》、《太平狗》、《松鸦为什么叫》;反映下岗女工生活的有《霓虹》、《口红》;等等。所有这些作品都瞄准了当代生活中某一方面的现实,反映了我们生活的不完美,看到了我们急需解决的问题。虽然苦难不是现实主义文学的唯一主题,但把当
代生活写进作品却是现实主义文学的特点。“它的显著特点,在于对现实的忠实;它不再造生活,而是把生活复制、再现,像凸面玻璃一样”, ⑦在于“毫无假借的直率,生活表现得赤裸裸到令人害羞的程度,把全部可怕的丑恶和全部庄严的美一起揭示出来,好像用解剖刀切开一样”。⑧现实主义“要求的不是生活的理想,而是生活本身,像它原来的那样”。⑨别林斯基的这些评价亦适于新世纪以来中短篇小说的创作,对现实的忠实是现实主义文学创作的生命力之所在。新时期以来农村发生的巨大变迁使乡土题材也出现了新的内涵。《野炊图》中三个告状钉子户的遭遇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不可
能存在,只有新世纪以来的社会现实才会出现,也只有新世纪以来的小说才会收纳近20年改革弊端的集中展现。《落果》中的亢永年也不同于《人生》中的德胜爷爷,更不同于高加林廉洁的叔叔,他一心想为乡人做点事,但他不能改变官僚体制的一分一毫,最终成为乡上瞎指挥的牺牲品。亢永年是经过八九十年代思想解放铺垫、人权思想观念熏陶的新世纪的乡村干部,但他的悲剧引人思索。对人的生存状态的关注是新世纪以来现实主义文学的一大主题,也是20世纪以来现实主义文学受现代派文学影响的一个表现。如《大老郑的女人》中,借助房东家的孩子的眼光审视改革开放以后生活中的事件与传统道德的冲突,用一种善意与宽容来表现大老郑生活中出现的这个女人的特殊身份,既体现出传统现实主义小说对生活的观察和对生活的理解,又有一种距离造成的间离效果。苦难叙事是现实主义的一面镜子,我们在《世界上所有的夜晚》中看到苦难的巨大破坏力,借用一个矿工生不见人、死不见尸的奇怪现状,揭示了现实背景下人权遭到践踏、个体生命价值不被尊重的现实。蒋百嫂的痛是
千百万矿工妻子的痛,也是我们当前社会的一个大大的伤疤。黑砖窑的现实存在又一次印证了人权遭到践踏的现状,从其表现来看,这仍然是新世纪的创痛。现实主义文学“所描写的人物和其现实中的范本的逼肖,或许不足以包括一切,但却是自然派的第一个要求,不做到这一点,作品里就不会有什么好东西”。⑩
我们回顾现实主义文学的每一次崛起,就会发现当生活出现大变革时,总是现实主义大发展的时机,因为现实主义与时代同步。19世纪的英国,贫富极端悬殊,劳资矛盾突出,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被社会力量挤压的小人物无助的命运成为作家们关注的重点。而俄国农奴制的反动、落后,对人性的戕害成为作家的重要主题,农奴制下普通人的悲惨命运也成为作家关注的重心。相比于19世纪的欧洲,我们如今的现实也是充满了变革时期的多种状态与混乱,如何把这些现实纳入作家的创作视野,必然成为现实主义文学的使命。谈到现实主义就不能不谈典型形象的问题。从中国现代文学中对典型形象的塑造看,吴荪甫、老通宝、林老板仍是至今令人难以忘怀的典型形象,他们是20世纪前半期中国社会特有的典型。尽管当代文学理论对典型形象的刻画已经淡化,但是,文学作品透过人物的刻画,反映广阔社会生活依然受到读者的青睐。陀思妥耶夫斯基说:“艺术始终高度忠实于现实”,“艺术不仅始终忠于现实,而且不可能不忠实于现代的现实。否则就不是真正的艺术。真正的艺术的特征就在于它永远是现代和大有裨益的”。 [11]忠于现实是艺术的基础, 但并不意味着艺术只是照搬生活。
“若要真实地摹写自然,仅仅能写,就是说,仅仅驾驭抄写员和文书的技术,还是不够的;必须能通过想象,把现实的现象表现出来,赋予它们新的生命”。[12]写实是现实主义的基础,但“没有思想的锋芒,不足以打破创作的温吞闷局;没有丰厚的艺术内涵,不足以抵达现代人需要的审美境界”。[13]当我们重翻近30年来的中短篇创作时,新世纪以来的现实主义小说在小说形式和小说技法的运用上趋于成熟和多样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塔铺》是1980年代有代表性的现实主义作品,小说展示了1978年恢复高考那一段特殊岁月中几个年轻人命运的转折,“我”、李爱莲、王全、“磨桌”、“耗子”,几种类型的高考生的表现由“我”的眼睛一贯到底,叙事扎实中透出单薄、线性。而迟子建的《世界上所有的夜晚》中矿工蒋百的故事是小说的重心所在,作者没有一上来就平铺直叙蒋百的故事,而是借用“文中作者”、“我”的眼光一层层揭开平凡生活底下深重的苦难。如果说《塔铺》中的“我”还极少与作家剥离的话,《世界上所有的夜晚》中的“我”已经自觉地成为作者塑造的一个形象,为作者和读者提供了一种把握客观世界和情感体验的角度或结构模式。“我”与蒋百等人的关系不大,但“我”是一个观察支点,使本来彼此孤立的材料获得秩序,成为一篇完整和连贯的本文。更为可
贵的是,作者没有流于一般的苦难揭示,而是把蒋百的遭遇与卖石头的小孩云领、能唱民歌的画家陈绍纯以及许许多多被准备“嫁死”的矿工们的遭遇都放在失去丈夫的“我”的视野之下,使蒋百的遭遇更富有一种时代和文化的内涵,让人们思考这个时代究竟是什么地方出了问题。厄普代克在1960年代评论博尔赫斯的创作时曾寄希望于博尔赫斯的创作风格“是否能够以其受到严肃对待的怪异,成为任何一种线索,引导我们走出当今美国小说那种死胡同式的自恋和彻底的无聊”。[14]现实主义
文学的回归或许对中国当代文学也能起到类似的作用。当代中国文学在多年追随欧美形式主义试验,尝试了众多的主义和无所适从之后,能否走出自己的路才是最重要的。拉美魔幻现实主义文学是现代主义运动与现实主义文学传统成功结合的一个良好范例。1960年代,拉美新小说在继承欧洲19 世纪
以来的现实主义文学传统的基础上吸收了法国超现实主义文学思潮的影响,把拉美神奇的现实和历史用魔幻现实主义的笔法展示出来,使20世纪的世界为之惊讶,也迫使大家重新思考文学的出路问题。中国当代文学的路怎么走? 如何让现实主义文学的新思维在中国文学的土壤上结出文学奇葩,则是我们拭目以待的大事。当下文学向方法论求证,众多的流派、众多的作家在现代主义、后现代
主义的大旗之下淡漠了传统现实主义文学的现实关注,在一片语义、句法与结构的海洋中颠簸。叙事视角、叙事层次的变化让读者与作者在多重参与中构筑新的文学堡垒,文学的语言学功能被强化,而文学作为守望者的功能却逐渐弱化,几乎被消解。反观20世纪世界文学,现实主义文学创作越来越受到重视,可以肯定,在方法的喧嚣之后,必有一个意义的回归。作家是一个时代的良知,这个责任是推卸不掉的。2005年歌德奖获得者、以色列作家阿莫斯·奥兹曾谈到,现代性已将一切差别改变,模糊了善与恶之间的分野,甚至否认恶的存在,将一切都归因于环境、心理、经济或道德的背景。他认为,就此而论,社会科学应为人们的决定、尤其是人类的苦难负责。他认为,虽然很难给善下一个定义,但恶自有其恶相。他相信我们每个人都有分辨善恶的能力。我以为,阿莫斯·奥兹的话其实是在批评当下文学创作的缺失。我们的生活不是尽善尽美,文学家应用自己的笔弘扬善鞭挞恶,这也是现实主义文学的使命。
①②③伊恩2P2瓦特著,高原、董红钧译《小说的兴起》第21、27、27页,三联书店1992年版。
④⑤伍蠡甫《西方文论选》(上)第148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年版。
⑥巴尔加斯·略萨著、赵德明译《谎言中的真实》第82页,云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⑦⑧⑨⑩[11][12]《西方文论选》(下) 第379—380、379—380、389、389、417页。
[13]《雷达自选集·文论卷》第351 页,山东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
[14]陈东飚等译《博尔赫斯文集·诗歌随笔卷》第285页,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1996年版。
(作者单位:兰州大学文学院、兰州城市学院中文系)
本文转载自《文艺理论与批评》2009年第3期
 最新评论
最新评论|
版权所有© 中外文学研究课题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