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版权所有© 中外文学研究课题组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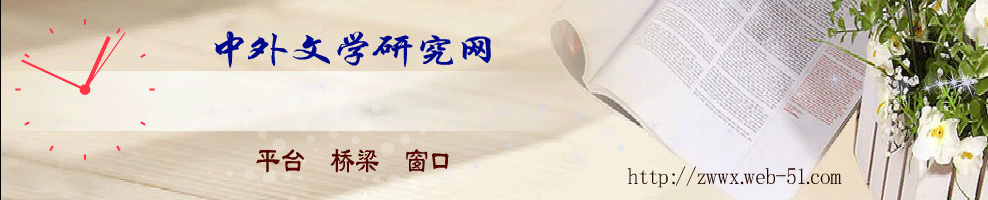
| 雷达:关于现实主义生命力的思考 |
| 中国网 china.com.cn 时间: 2009-11-10 发表评论>> |
|
纵观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不难发现,六十年来,真正有生命力、经得起时间淘洗的作品,大都是坚持了现实主义精神,具有勇气和胆识的,努力维护了文学的自由审美品格的作品。这里所说的现实主义,就是对时代生活、人民疾苦和普通人命运的密切关注,对人的生存境遇的密切关注,对民族灵魂的密切关注,为此它勇敢地面对,真实大胆地抒写,以至发出怀疑和批判的声音。比如在十七年文学中,“左”倾思潮确有愈演愈烈的趋势,于是被认为这个时期的作家的主体意识普遍沉睡甚至完全没有。然而,这并非事情的全部。现在看来,主体意识在一些作家身上不但存在着,且无时无刻不在寻求突围。一些作家早就在抵制直接的、短视的,配合式的创作,反对公式化,概念化的创作,坚持直面地,大胆地写出真实,塑造有血有肉有灵魂的人物。由于作家坚持了现实主义的精神和审美的立场,于是对人性人道的思考就往往会逸出“政治”的堤坝,无意中与“时代”抗辩,达成了某种超越性。这些坚守和努力,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像《洼地上的战役》(路翎)、《我们夫妇之间》(萧也牧)、《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王蒙)、《改选》(李国文)、《红豆》(宗璞)等等,就都有突出的、鲜明的表现。 但事物总是复杂的和缠绕的,现实主义生命力的奥秘也同样复杂。当时一些政治意识很强的、惟写工农兵和满足无产阶级政治需要的宏大叙事,其中一小部分成为了今天所谓红色经典者,在今天就依然拥有一定的生命力,有一些成为改编者的丰厚资源,当代人津津乐道的对象,甚至偶像,这该怎么看?这不禁使我们思索:当时的“政治视角”对艺术来说,是否具有既束缚又无意中成全了它的艺术生命的两面性?新时期以来,“政治视角”几乎一度被作家们忽略或远离,事实上,政治是社会的焦点所在,要揭示一个时代的本质,不触及政治便是逐本求末。政治并非单纯地表现为国家制度、政党存在,在本质意义上它是一种文化精神的存在。另外,当时确有不顾作家的风格、个性和消化能力,一律赶到“火热的斗争生活中去”的做法,但这并不能改变生活是创作唯一源泉的真理性,事实证明今天深入生活依然是文学创新的根本性问题。当时把作家的生活体验性和亲历性强调到了极端,是否在造成拘泥原型之病的同时,“逼”出了大量真实鲜活的细节? 现实主义精神应该是变动不居的,是随时代的发展而发展的,只有不断地更新和变化,才能保持它的活力和张力。应该看到,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对现实主义的理解,较多地停留在呼唤写真实,直面现实,干预生活,反对直接的配合性写作上;七八十年代之交,回归现实主义传统,先是把焦点集中在能否说真话,写真事上,随着思想解放运动的深入,才进入了发现人、关注人、尊重人,人是灵魂的层面。新时期文学三十年最大的成就,也得之于此。现代主义也关心人,焦虑人的处境,但与现实主义是不同的,它对现实主义不无启迪。正是围绕着发现人、尊重人,刘心武的《班主任》重新发出了“救救孩子”的呐喊,徐迟的《哥德巴赫猜想》重塑了知识分子的精英形象,我们在这里听到了新启蒙的声音。 与现实主义精神相伴,民族灵魂的发现这一主题还在深入。我们看到,八十年代中期,现实主义文学仿佛又一次来到十字路口:是大胆的自我更新,还是故步自封,是开放吸纳,还是原地踏步,这是个考验。现实主义要不要在与现代主义的碰撞中丰富自己,要不要吸收域外的有益的哲学和文学观念,要不要在文化精神上向纵深拓展?回答是肯定的,因而有了一次腾跃。1985年,《人民文学》发表了刘索拉的《你别无选择》,徐星的《无主题变奏》,韩少功的《爸爸爸》,阿城的《孩子王》等。在全国其他刊物,还有许多重要的文本发表。《你别无选择》被有的理论家认为是“中国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现代派作品”,但我从小说所写音乐学院内在紧张的精神冲突中感受到的,主要还是“五四”个性自由精神在当代的回荡。《爸爸爸》回转身来,续接国民性批判的主题,沿着地域的河流,向着民族文化性格的根因追溯。而在莫言的《红高粱》里,作家有感于“种的退化”,重塑农民英雄形象,呼唤生命强力,复活民族的野性的游魂。对现实主义的发展来说,也许路遥的《平凡的世界》是更为典型的文本,它作为文学上的柳青之子,可以明显感到它与十七年现实主义的血缘关联,路遥确实继承了不少东西,但是,他又有所扬弃,提供了一种内在的现代性视角,那就是对现代农民人格的呼唤和初塑。 九十年代以来,特别是迈入新世纪的中国,市场经济和商品化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卷来,全球化进程的加剧,“加入世贸”的重大影响,城市化、高科技化、网络化的急剧推进,正在极大地改变着人们的生存方式和就业、居住方式,改变着人们的时空观念、思维方式以至道德伦理情感。中国社会的精神生态更趋物质化和实利化,思想启蒙的声音在文学中日渐衰弱和边缘,小说大多走向了解构与逍遥之途,走向了世俗化的自然经验陈述和个人化的叙述。与之相伴,一个大众文化高涨的时期来到了。就文学来说,现实主义还能不能向前发展?特别是对人的发现,这个二十世纪贯穿至今且不断深化的重要精神课题,今天还有没有新的发现,对现实主义来说,将是决定性的因素。这也应该是衡量一个大作家与凡庸作家的标准。事实上,在今天,作家选择时代,其实就是选择“人”,发现“人”,发现一种生存状态和精神状态。有一种说法,认为新世纪的“人”既不同于八十年代的“理性”的人,也不同于九十年代新写实的“原生态”或“欲望化”的人,而是“日常”化了的人。这种说法有一定道理。近些年有的作品之所以有所深化,就在于更加注重于“人的日常发现”,并以“人的解放”、“人的发展”作为“灵魂重铸”的内在前提和基础。然而,对人的深刻理解与表现,又与深切的生活体验无法分开。网络的海量信息固然给写作者带来极大便利,但它永远不可能代替作者的亲历的感受和心灵的共振,因为那不是身上的骨头和肉,而创作需要生命的投入。 在今天,我们不能不关心文学的现实处境。人们常说以往文学的轰动效应,多是借助于敏感的社会问题,承担了自身以外的任务,现在文学才真正回到了它应有的位置,现在的秩序才是文学的正常秩序,因而无须慨叹文学的边缘化。这样说当然是明智的,不无合理性,但也并不尽然。文学不能借此安于现状,看不到危机,满足于被动的生存。在今天,谁不努力展示自身的魅力,就没有谁的位置,这是很无情的。其实,世界上有些发达国家,纯文学的销量和覆盖面是非常可观的。现在,网络文学、市场化出版、青春文学、类型化写作、大众读物,在普通读者中拥有更大的份额,其销售量是一般纯文学无法想象的。像《明朝那些事儿》、《藏地密码》、《鬼吹灯》、《诛仙》、《杜拉拉升职记》等大众文化之作,或一些带有较强消遣性,娱乐性,猎奇性的书,正在创造发行奇迹。这些作品当然有它们满足大众需要和它生存发展的必然性。但是,它们确也造成了阅读的分化,比如传统文学读者稳中有降。文学特别是纯文学,应该怎样选择和认定自己的角色呢?文学的审美价值和精神追求应该在一个什么样的向度上?究竟是向那些作品倾斜,为其所改造、所置换,削减原有的一部分功能,强化另一些实用功能,还是坚持原有的一贯稳定的精神价值,包括发扬现实主义的精神,就不仅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一个尖锐的实践问题。 诚然,只要人类还存在着良知和情感,文学就不会消亡,我们大可不必悲观;但究竟文学选择什么样的方式,深刻地表达什么样的情感,确也决定着文学的命运和存在的理由。现在作家的选择无疑宽广得多,自由得多,但这里仍有个对时代重大精神问题是否回避,仍然有高下之分和文野之分,厚重和轻飘之分。在我看来,最有分量和最有价值的文学,应该是关注人的存在境遇,展示民族的灵魂和心史的,直指人心的,具有形而上追求的文学。越是这样,在这个物化的时代,文学就越是不可替代,就越有生命力。 今天,我们面临一个社会、文化大转型的时期,同样也是一个与世界文化碰撞、融合、重构的时期,这样一个时期在中国历史和人类历史上也并不多见。这不仅是作家创作的难得机遇,同样也是作家面临的最大困难。历史上,无论哪一个国家,在每一个转型期和文化的融合期,恰恰也是文化兴盛的时期,如我国的春秋战国时期、魏晋时期、隋唐时期、五四时期。我认为,现实主义肯定是我们的选择之一。但是,现实主义怎样发展,却是需要探索的新难题。 当然,现实主义始终是一个争论不完的话题。除了针对现实存在的问题之外,我们还应该更多地追问一些基本的问题:如什么是文学?什么是人民的文学?今天的人面临什么困境?应该怎样增大文学的精神性内涵?今天的大众需要什么样的文学?等等。这些基本的问题可能会帮助我们廓清文学上的一些迷雾,对当下的文学的创新将是极其有益的。 |
| 文章来源: 人民网-《人民日报》 |
 最新评论
最新评论|
版权所有© 中外文学研究课题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