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版权所有© 中外文学研究课题组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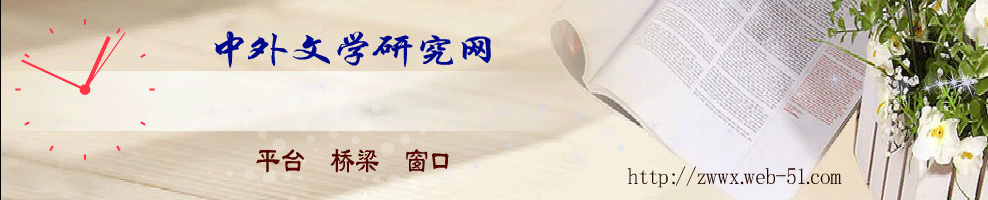
| |||
| 我追随前辈,走上比较文学之路,是偶然,也是必然。70年代中期,北京大学招收了一些留学生,我被分配去教一个留学生班的现代文学。我的这个班20余人,主要是欧美学生,也有从澳大利亚和日本来的。为了给外国学生讲课,我不能不突破当时教中国现代文学的一些模式,我开始讲一点徐志摩、艾青、李金发等“资产阶级”作家。为了让我的学生较深地理解他们的作品,我不得不进一步去研究西方文学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影响以及它们在中国传播的情形。这一在学术界多年未曾被研究的问题引起了我极大的兴趣。我开始系统研究20世纪以来,西方文学在中国是如何被借鉴和吸收,又是如何被误解和发生变形的。 从对早期鲁迅和早期茅盾的研究中,我惊奇地发现他们不约而同都受了德国思想家尼采很深的影响。再进一步研究,发现这位30年来被视为煽动战争,蔑视平民,鼓吹超人的极端个人主义者尼采的学说竟是20世纪初中国许多启蒙思想家推动社会改革,转变旧思想,提倡新观念的思想之源。无论是王国维、鲁迅、茅盾、郭沫若、田汉、陈独秀、傅斯年等都曾在思想上受到尼采深刻的影响。事实上,尼采学说正是作为一种“最新思潮”为中国知识分子所注目。尼采对西方现代文明的虚伪、罪恶的揭露和批判,对于已经看到并力图避免这些弱点的中国先进知识分子来说,正是极好的借鉴。他那否定一切旧价值标准,粉碎一切偶像的破坏者的形象(这种形象在中国传统社会从来未曾有过),他的超越平庸,超越旧我,成为健康强壮的超人的理想都深深鼓舞着正渴望推翻旧社会,创造新社会的中国知识分子,引起了他们的同感和共鸣。无论从鲁迅塑造的狂人所高喊的“从来如此——便对么?”的抗议,还是郭沫若许多以焚毁旧我,创造新我为主题的诗篇,都可以听到尼采声音的回响。但是尼采学说本身充满了复杂混乱的矛盾,他的著作如他自己所说,只是一个山峰和另一个山峰,通向山峰的路却没有。各种隐晦深奥的比喻和象征都可以被随心所欲地引证和曲解。因此,尼采的学说在不同时期也就被不同的人们进行着不同的解读和利用。 1981年,我根据上述理解,写了一篇《尼采与中国现代文学》发表于北京大学学报,引起了相当强烈的反响。客观他说,这篇文章,不仅引起了很多人研究尼采的兴趣,而且也开拓了西方文学与中国文学关系研究的新的空间。1986年,北京大学第一次学术评奖,这篇文章还得了一个优秀论文奖。事隔五六年,还有人记起这篇文章,我很觉高兴。后来,它又被选进好几种论文集,并被译成英文,发表在澳大利亚的《东亚研究》上,与研究尼采同时,我编译了一本《国外鲁迅研究论集》(北京大学版社,1981)。由于和留学生接触,我看到了许多国外研究鲁迅的论文,我的英语也有所长进。30年的封闭和禁锢,我们几乎和国外学术界完全隔绝,我在这些论文中真像发现了一个新天地。我感到这些论文在某些方面颇具特色。例如谈到鲁迅的思想变化时,把鲁迅和一些表面看来似乎并无关联的西方知识分子如布莱希特、萨特等人进行了比较,指出他们都甘愿牺牲舒适的环境去换取不确定的未来;他们都不相信未来的“黄金世界”会完美无缺;也不想从他们正在从事的事业索取报偿;他们理性的抉择都曾被后来的批评家们误认为一时冲动或由于“绝望”,甚至是受了“现代符咒——革命”的“蛊惑”!这样的比较说明了鲁迅的道路并非孤立现象,而是20世纪前半叶某些知识分子的共同特色。这部包括美、日、苏、加拿大、荷兰、捷克、澳大利亚7个国家,20篇文章,并附有《近二十年国外鲁迅研究论著要目》(270篇)的《国外鲁迅研究论集》对国内鲁迅研究,也许起了一些开阔视野,促进发展的作用;对我自己来说,则是使我初步预见到对并无直接关系的不同文化之间的文学作品进行“平行研究”的巨大可能性。我于1987年写成的一篇论文《关于现实主义的两场论战——卢卡契对布莱希特与胡风对周扬》就是沿着这样的思路来写的。这篇文章1988年发表于《文艺报》,同年10月为《新华文摘》所转载。在1988年国际比较文学第12届年会(慕尼黑)上,我提交了这篇论文,后来被选入了大会论文集。 1980年以来,北京大学的季羡林、李赋宁、杨周翰、杨业治、金克木等教授都对比较文学表示了程度不同的兴趣,加上当时杨周翰先生的博士生张隆溪和我,还有一些别的人,我们一起于1981年1月成立了中国第一个比较文学学会——北京大学比较文学研究会,由季羡林教授任会长,钱钟书先生任顾问;我则充当了马前卒,号称秘书长。学会生气勃勃,首先整理编撰了王国维以来,有关比较文学的资料书目,同时策划编写《北京大学比较文学研究丛书》,并出版了《北京大学比较文学研究会通讯》。 这年夏天由于一个很偶然的机会,我得到了美国哈佛一燕京学社的资助,去哈佛大学进修一年。我对哈佛大学比较文学系向往已久,这不仅是因为它的创办者之一白璧德教授(Irving Babitt)对于东西方文化的汇合曾经是那样一往情深,也不只是因为20年代初期由哈佛归来的“哈佛三杰”陈寅恪、汤用彤、吴宓所倡导的“昌明国粹,融化新知”为东西文化的汇合开辟了一个崭新的学术空间,还因为1981年正在担任哈佛东西比较文学系系主任的纪延教授(ClaudioGumen)多次提到:“我认为只有当世界把中国和欧美这两种伟大的文学结合起来理解和思考的时候,我们才能充分面对文学的重大的理论性问题。”他的这一思想深深地吸引了我。遗憾的是在哈佛的一年,由于我的英语不够好,我始终未能和纪延教授深入讨论我想和他讨论的问题,但我却大量阅读了比较文学的基础理论和有关资料,进一步提高了我的英语水平。 1982年和1983年,我有幸被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邀请为客座研究员,在那里,我结识了白之教授(Cyril Birch)和斯但福大学的刘若愚教授(James Liu)。著名的跨比较文学系和东亚系的白之教授是我的学术顾问,他对老舍和徐志摩的研究,特别是对他们与外国文学的关系的研究都给了我很大的启发。我很喜欢参加白之教授的中国现代文学讨论班。印象最深的是有一次讨论赵树理的小说《小二黑结婚》。同学们各抒己见,谈谈各自对书中人物的看法。一位美国学生说,她最喜欢的是三仙姑,最恨的是那个村干部。这使我很吃惊,过去公认的看法都认为三仙姑是一个四十多岁,守寡多年,还要涂脂抹粉,招惹男人的坏女人;村干部则是主持正义,训斥了三仙姑。但这位美国同学也有她的道理:她认为三仙姑是一个无辜受害者。她也是人,而且热爱生活,她有权利追求自己喜欢的生活方式,但却受到社会的歧视和欺压;村干部则是多管闲事,连别人脸上的粉擦厚一点也要过问,正是中国传统的“父母官”的模式。我深感这种看法的不同正说明了文化和社会价值观念的不同。这种不同不仅无害,而且提供了理解和欣赏作品的多种角度。正是这种不同的解读才使作品的生命得以扩展和延续。这个讨论班给我提供了很多这类例子,使我在后来的比较文学教学中论及接受美学的原理时有了更丰富的内容。 在伯克利的两年里,我精读了执教于斯坦福大学的刘若愚教授所写的《中国诗学》和《中国文学理论》以及他关于李商隐诗的一些相当精辟的论述,并和他进行过多次讨论。他对中西诗学都有相当深的造诣,他的思考给了我多方面的启发。首先是他试图用西方当代的文学理论来阐释中国具有悠久历史的传统文论,在这一过程中确实不乏真知灼见,而且开辟了许多新的研究空间,但是,将很不相同的、长期独立发展的中国文论强塞在形上理论、决定理论、表现理论、技巧理论、审美理论、实用理论等框架中,总不能不让人感到削足适履,而且削去的正是中国最具特色、最能在世界上独树一帜的东西。其次,我感到他极力要将中国文论置于世界文论的语境中来进行考察,试图围绕某一问题来进行中西文论的对话,得出单从某方面研究难于得出的新的结论。事实上,这两方面正是我后来研究比较文学的两个重要路向。 1984年夏天我回国,中国的比较文学研究已经有了新的进展:1981年,辽宁省率先成立了全国第一个地方性比较文学研究会,并在三年内,接连开了三次学术讨论会;1983年6月,在天津召开的外国文学学会年会上,举办了一次全国性的比较文学讨论会;紧接着,第一次中美双边比较文学研讨会在北京召开(1983年8月),大会由钱钟书先生致开幕词,刘若愚、厄尔·迈纳(Earl Miner)、西里尔·白之(Cyril Birch)和王佐良、杨周翰、许国璋、周王玉良、杨宪益等世界著名教授都参加了大会。看来,成立全国比较文学学会的时机已经成熟,1985年10月,由35所高等学校和科研机构共同发起的中国比较文学学会在深圳大学正式成立,大会选举季羡林教授担任名誉会长,杨周翰教授担任会长。从此,中国比较文学走上了向“显学”发展的坦途。(摘自《跨文化之桥》,乐黛云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3月)
|
 最新评论
最新评论|
版权所有© 中外文学研究课题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