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版权所有© 中外文学研究课题组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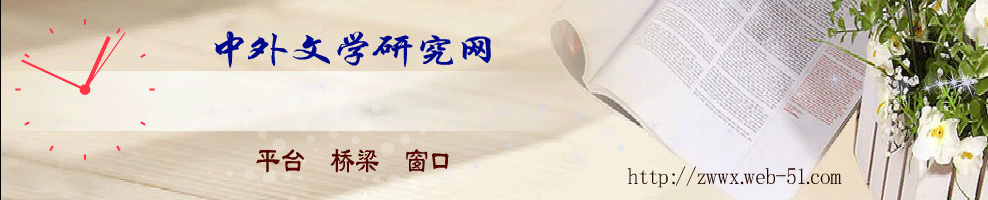
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 周小娟
在中国现代儿童文学的发展过程中,日本与中国颇有渊源。从中国儿童文学的贡献者来看,鲁迅、周作人、郭沫若、穆木天、徐蔚南、谢六逸等均为留日学生,这些学者的儿童文学观受到日本儿童文学的启发。从儿童文学作品的译介来看,1930至1940年间,有《日本故事集》(1931)、《日本童话集》(1931)等近二十部日本儿童文学作品译入中国。作为外国儿童文学作品中译的媒介,徐傅霖据岩谷小波选编本译“世界童话”,唐小圃据昇曙梦编本译俄国童话,另外在现代中国产生重要影响的俄苏爱罗先珂童话剧《桃色的云》、班台莱耶夫的儿童小说《表》、奥地利作家至尔·缪伦的童话作品,以及意大利亚米契斯的儿童小说《爱的教育》等参考了日译本转译。另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是,从儿童文学理论来看,在20世纪30年代,两部日本儿童文学理论著作《世界童话研究》和《童话与儿童的研究》被译入中国,而这在我国各时期的儿童文学史中并未展开介绍,应该说,这两部译著也适时地推进了中国现代儿童文学理论的发展。
1929年,日本作家、儿童文学理论家芦古重常的《世界童话研究》由留日回国的黄源译出,1930年3月由上海华通书局出版。1932年第7卷第5期的《中华图书馆协会会报》的“新书介绍”栏目介绍道:“是书萃世界著名童话于一炉而冶之,内分古典童话,口述童话,艺术童话三大篇,于作家之身世,作风,及其影响于世界文坛,皆有极准确深切之叙述,儿童最良之读物也。”[1]日本用“童话”来指称广义的儿童文学,因此这是我国翻译的第一本全面介绍外国儿童文学的理论著作。赵景深在序言中指出“一切重要的神话传说故事寓言,都会恰如其分的论到。”[2]从童话发生学的角度,将研究对象分为古典童话、口述童话和艺术童话,研究范围为童话的起源论、童话的形式论、童话的内容论、童话的应用法、童话的讲法、童话的历史。分三个部分论述:第一编论述古典童话,主要包括印度故事、希腊神话、北欧神话、犹太神话、基督教神话、天方夜谭、伊索寓言。第二编是口述童话,包括格林童话、阿斯皮尔逊的童话、英格兰童话、克勒特族的童话、法国童话、意大利童话、俄国童话。第三编是艺术童话,包括贝洛尔童话、豪夫童话、安徒生童话、克雷洛夫寓言、托尔斯泰童话、王尔德童话。
《世界童话研究》一方面从宏阔的视野对童话的发生、发展和成熟的历程做出梳理,另一方面对具体作家作品进行了细致深入的研究和评价,处处渗透着“比较”的眼光。如概括格林童话的价值在于“世界上最杰出的典型的口述童话集。”相较而言,安徒生在艺术童话的地位也无可比拟,其特征“(一)是独创的,(二)是雄大壮丽,(三)有优美而透彻的情绪,(四)是卓越的文章与轻妙的幽默,(五)是宗教的思想。”[3]值得一提的是芦古重常精妙的作品分析,从基督教的观念出发,认为安徒生童话中最杰出的是《小女人鱼》(The Lillte Sea Maid)和《雪女王》(The Snow-Queen)。同是取材于人鱼的童话,《小女人鱼》和王尔德的《渔夫与他的魂》不同,王尔德是“力说恋爱的最后的胜利,”安徒生“既写着恋爱的力量而又说着抑情主义。”而王尔德的《幸福王子》“在充满着暖意爱情与童话意匠的巧妙之点,便是在安徒生也是难得之作。”[4]芦古重常的文本分析极有见地,遗憾的是,在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对于安徒生的评价已经集中于对其“空虚的思想”的批判上,芦古重常的观点并未得到回应。1933年赵景深在務本女学师范科作了题为《儿童文学女作家》的讲演,介绍了西方自18世纪到20世纪的儿童文学女作家,讲演稿在1933年第3卷第3期的《青年界》刊出,其中介绍都娜夫人和乔治·桑时引用了芦古重常的这部专著,可见本著作对中国知识界了解外国儿童文学起到了参考作用。
另一部理论著作是钟子岩译日本神话学者松村武雄的《童话与儿童的研究》,1935年由开明书店出版。1936年第6期的《图书展望》杂志介绍本书“作者松村武雄,为日本文学界巨子,本书乃从下列三方面作深入之研究:(一)儿童的心理与生活的研究;(二)童话的民族心理的、民俗学的、史的研究;(三)未开化民族的心理的研究。观此则作者文学智识之丰富渊博,可以想见。”[5]著作分十二个部分:绪论;童话的哲学;儿童的本能和创造的反应;童话剧的研究;童话的种类和意义;当作文艺的童话的内容及形式论;儿童的生活及心理和童话的关系;儿童的心的发达阶段和童话;童话的制作改作选作的原则和方法论;童话的教育的价值与发挥价值的方法;故事讲述术的研究;故事讲述的成败的诸因子的考察。本著作堪称一本全面的儿童文学研究之作。值得一提的是,在“关于童话的选择的原则和方法论”部分,列举了日本、中国、印度和欧洲的相关作品作为可选择的童话材料,在“汉文书”部分提到以下读物:《史记》、《三国志》、《水浒》、《吴越军谈》、《聊斋志异》、《搜神记》、《搜神后记》、《述异记》、《博异记》、《三国演义》、《酉阳杂俎》、《大藏经》等,对世界各国尤其是中国古代童话因子的介绍,足以见出作者深厚的学术功底。事实上,本著作在中译之前就已受到关注,书中将“童话”分为九类:幼稚园故事、滑稽谈、寓言、神仙故事、传说、神话、历史谈、自然界故事、实事谈。1926年徐如泰发表在《中华教育界》第16卷第5期上的文章《童话之研究》,将童话分为神话、故事、滑稽话、寓言、传说、历史谈、实事谈、自然童话等八种,此处的“童话”延续了日本的童话概念,即广义的儿童文学,在分类上除幼稚园故事并未出现,其余与松村武雄的分法基本一致。1931年,朱文印的文章《童话作法之研究》与松村武雄专著中“关于童话的制作的原则和方法论”论述几乎完全一致,陈伯吹与陈济成所编《儿童文学研究》中“童话研究”一章也基本上采用了以上论述。[6]可见,在本书译介之前,我国儿童文学界已有意识地借鉴了日本的相关理论。
1937年,在槙本楠郎的文章《日本童话界之现状》中谈起日本的儿童文学理论,“可以称为儿童文学的专门批评家的,一个人也没有。”虽然有两位研究者芦古重常和松村武雄,但“想从他们的研究中学取‘童话’的‘文学理论’不是容易的事。”[7]槙本楠郎站在建设日本新儿童文学的立场,对从事传统儿童文学研究的学者作出如此评价。但从中国儿童文学理论发展的角度,自20世纪20年代到30年代中期,张圣瑜、赵侣青、徐迥千、王人路、陈伯吹、陈济成等先后出版理论著作,另有大量儿童文学批评文章问世,这与欧美的影响,以及对日本儿童文学理论的借鉴有着密切的关联,因此《世界童话研究》和《童话与儿童的研究》对中国儿童文学理论发展的影响不应被忽视。
 最新评论
最新评论|
版权所有© 中外文学研究课题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