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版权所有© 中外文学研究课题组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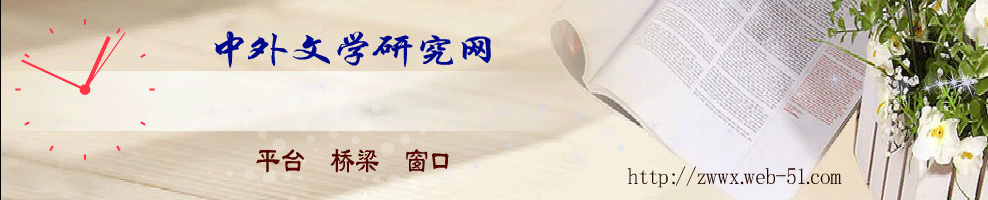
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 杨佩珍
摘要:莎士比亚笔下的奥赛罗和李龙云剧中的马兆新虽是相异历史时期及不同文化背景书写下的悲剧人物,但二者在剧中无不以愤恨而哀切的行动来将命运困厄之下的心理风暴呈现出来。他们面临着相似的精神困境——对理想生命状态遭遇破碎的痛苦与无奈,他们在自我的内心挣扎中陷入了更深的焦躁与彷徨,进而酿成了悲剧的人生。笔者将着眼于奥赛罗和马兆新悲剧人生的成因这一基点,分别从二人的身份意识、主体体认、思想困顿这三个方面来对他们的悲剧命运进行比较研究,以期发现人物相通而又各异的价值追寻与生命体悟历程。
关键词:奥赛罗 马兆新 身份意识 主体性 心灵困顿
《奥赛罗》是英国文艺复兴时期伟大的剧作家莎士比亚(1564~1616)的四大悲剧之一,是莎士比亚大约于1603年写作的。奥赛罗是供职于威尼斯政府的摩尔族贵裔,他与元老勃拉班修的女儿苔丝狄蒙娜相爱,但他因是黑人而受到他人歧视,他们的相爱也不被勃拉班修看好,所以他俩只得秘密地在一起。奥赛罗手下的旗官伊阿古是一个不安于世的人,他因奥赛罗将副将职位给了凯西奥而心怀不满,先是到勃拉班修跟前告发奥赛罗与苔丝狄蒙娜,不料却促成了两人的婚事。继而他又设计陷害苔丝狄蒙娜,告知奥赛罗并使其相信苔丝狄蒙娜与凯西奥之间有私情,奥赛罗在愤恨之中错杀了苔丝狄蒙娜,后来经伊阿古的妻子爱米利亚揭露真相,奥赛罗遂在愧悔之中以剑自刎。
马兆新是中国当代剧作家李龙云(1948~2012)于1987年创作的话剧《荒原与人》(《洒满月光的荒原》)中的主人公,剧作中十五年后的马兆新与十五年前的马兆新同时存在,在他今昔的心理流变中,我们看到了文革特定背景下北大荒落马湖上的世态人情。十五年前的马兆新因心爱之人细草被连长于大个子(于常顺)奸污而处于矛盾、彷徨、嫉妒的复杂情绪之中,他后来因无意间烧毁苫草垛而逃出了落马湖,当他回到落马湖时细草因羞于怀有于大个子的孩子而决定嫁给底窑小屯的一个马车夫。马兆新最终怀着凄惘而痛楚的心情走上了十五年流浪的漫漫路途……
一、身份意识统摄下的心灵痛苦
《奥赛罗》和《荒原与人》这两部悲剧中,主人公悲剧命运的形成原因可以从不同的角度生发出各异的因由。笔者在这一部分主要立足于奥赛罗和马兆新二人的身份体认这一视角,从他们所处的环境以及各自基于男性身份的认知与表现这两个元素的分析来探求二人在心理流变历程中的矛盾与挣扎。
奥赛罗作为骁勇善战的将领为威尼斯政府作出了值得称颂的贡献,正如他自己在剧中所说“世人还没有知道——要是夸口一件荣耀的事,我就要到处宣布——我是高贵的祖先的后裔,我有充分的资格,享受我目前所得到的值得骄傲的幸运。”①但剧中他人的言语之却间充斥着对他的不屑和抵触:伊阿古称他为“黑将军”“走江湖的蛮子”,罗得利哥(苔丝狄蒙娜的追求者)说他是“漂泊流浪的异邦人”,勃拉班修则直接痛斥他为“丑恶的黑鬼”。我们能够注意到的是对于威尼斯人来说奥赛罗是他国人,相应的在奥赛罗的处境里,威尼斯的众人又成为他的对立方。“《奥赛罗》的一个焦点是奥赛罗文化认同的迫切要求和白人社会对他的认同要求的抵制这两者之间的直接冲突。”② “黑”“摩尔人”这些标签是威尼斯人联合起来对他的鄙夷与钳制,是身为异族而被放置在他文化之中的尴尬与哀痛。
苔丝狄蒙娜的倾心使奥赛罗暂时与身为异族人的卑弱感拉开了一定的距离,但伊阿古却用巧妙的言辞重新勾起了他的怀疑与后怕,“说句大胆的话,当初多少跟她同族、同肤色、同阶级的人向她求婚,照我们看来,要是成功了,那真是天作之合,可是她都置之不理,这明明是违反常情的举动;嘿!从这儿就可以看到一个荒唐的意志、怪癖的习性和不近人情的思想。”③这些话在表面上看来是伊阿古别有用心的陷害,实则暗示了奥赛罗试图摆脱的身为异族人的心理阴影,他的心底因存在这种思想的因子所以才会被诱发出巨大的愤怒。“对于自己所处的地位,他感到深刻的身份认同危机。他深知自己始终是白人主流社会的‘异类’ ——从跨文化角度看的‘他者’。”④归根到底奥赛罗作为摩尔人的身份一直在潜伏在他的思维领域,伊阿古正利用了他因身份地位而感到的卑弱进而对他的心灵造成了钳制与束缚,最终使得让他在这种心理折磨中毁灭自己。
让我们将眼光收回到奥赛罗与苔丝狄蒙娜因爱恋而建立起来的家庭上,他们的关系虽然得不到勃拉班修的认可,但奥赛罗自觉放弃了自由自在的生活而缚就了家室的羁缚,在真诚而炽热的爱恋中与苔丝狄蒙娜结合在了一起。但当他一步步走向伊阿古替他设下的陷阱的同时也渐渐走向了心里怀疑的怪圈而难以自拔,他在痛苦挣扎中开始深深厌恶当初自己结婚的选择,“啊!结婚的烦恼!我们可以在名义上把这些可爱的人儿称为我们所有,却不能支配她们的爱憎喜恶!”⑤他因难以摆脱的心灵纠结而怀疑一切,这正是他作为丈夫的立场对妻子忠贞期望的破碎与无望。
奥赛罗的爱恋是脆弱而经不起风浪的,当他对纯洁坚贞的爱情期望受到来自外界话语的倾覆时,他就陷入了男性权威的施展与作为异族人被排挤之间的困厄境地。他以与苔丝狄蒙娜的结合抚慰他身为异邦黑人的心理创伤,可当理想的爱情遭遇破碎化之后,他的精神面临着更加难堪的双层钳制——伴随在爱的幻灭之后的便是他身为异邦人的更加边缘化与无所依存感的产生。奥赛罗在威尼斯上层社会亦步亦趋,他的将军头衔赘述着他身在白人社会的一种屈服与无奈,他的爱恋婚姻又笼罩在他者的言语威势之中。作为异邦人,他是孤寂而卑弱的,作为男性的他却又在种族、阶级、年龄的交相纠葛之中亲手毁灭了爱的对象苔丝狄蒙娜,进而毁灭了他自己。
在《荒原与人》这部剧中,马兆新和细草都是深入北大荒落马湖的知识青年,他们的青春与渴望在落马湖荒原上默默地生根发芽,又在那古荒深处无声飘落。“北大荒不仅成为一代人青春的祭场,更造成了信仰的断代。”⑥马兆新是时代潮流中的一颗微粒,他的人生方向被特定的历史所决定——为神秘荒原的垦荒事业奉献青春的力量,这是身在其时被群体性的他者所归置的生命定向。
马兆新与同处荒原的年轻人一样被剥夺了思考的空间与时间,他失去了对自我生命价值的探寻机会,就像十五年前与十五年后未曾变化过的印在荒原上的两道爬犁辙一样,时空在不停歇地延伸,但是他人生的痕迹、青春的印象全然湮没在一片苍茫的寂寥之中。《荒原与人》的时间被设定为“人的两次信仰之间的空间”,马兆新无法跨过时间的辙沟去寻找迷失的自己,因为即便时间退回去,也无法阻挡命运的裹挟,“一切似乎都是从那个秋天开始的!……人感到失去了归宿,人性失去了平衡,人在茫然不知所措之中开始疯狂地寻找自我……”⑦这是无法选择的开始,这是难以抉择的自我迷失。他所处的时空决定了他的身份以及基于此身份的人生导向,他像打磨好的砖块一样被放置在了统一的建设堡垒之上,同时也被深深地禁锢了起来。“我是一颗小草,一颗荒原上的小草。春风吹过,荒原处处都是我的家,秋风刮过,荒原没有我的家……”(私生女毛毛的歌声)落马湖荒原的神秘辽远构成了对马兆新内心意识的第一层挑战,人在面对无法预知的自然洪荒之景时既有由衷的赞美与钦赏,同时也多了一层对生命的难以把握和无所归属的心理体验。
落马湖王国中的国王于大个子在剧作中是一个对他者的命运起到绝对钳制作用的人物,他是织就隐形罗网上必不可少的经与纬,他是框束年轻人的有形实体。他通过用链轨轴敲打耙片(起到钟的作用)让知青们聚集来,进而传达他的种种“旨意”,剧作开头的场景部分写到的“那不是一口钟,而是落马湖王国皇权的象征!是一个绞刑架!”直接而有力地凸显出了权力对人性的压制与戕害。于大个子的存在几乎造成了剧中所有人物的遭难——他对细草的奸污导致细草与马兆新爱情理想的幻灭,他因公开苏家琪与李天甜的书信而造成李天甜葬身于落马湖的沼泽之中,他对邢福林和四川女人的故意刁难……他就像通体充盈巨大能量的幽灵一般控制着落马湖所有人的生命状态,马兆新只能用怀疑和愤恨的情绪去反抗由于大个子造成的难以愈合的情感创伤。他虽借苏家琪与李天甜的书信将被搜查之际表现出了他难忍的怨怒(怀着激愤的心情烧苏家琪和李天甜的信件、日子、一枚小小的丘比特,只不过没有彻底烧毁),但他微弱的抗争无法撼动于大个子的强势存在,他最终向命运低头,忍痛看细草嫁给陌生的男人。
在于大个子的控制之下,马兆新是一个卑弱而无奈的个体存在,在上与下、强与弱这种鲜明的身份对立之中,他的行动力一再屈服于于大个子的强势权威。在这个心酸压抑的生命进程中,他的心理状态是渴望探寻出路而不得的纠葛,是期盼获得新生的无望。于大个子像一个鬼魅的影子一般横梗在他与细草之间,缠绕着在他的思想,使他只能在愤恨和怨怒之中自怨自艾、挣扎徘徊。
当我们的眼光投射到细草与马兆新这对恋人身上的时候,除了同情他们哀凄的爱情,更多的是对爱情理想破灭的一种深思。假如没有于大个子的插足,马兆新与细草或许可以建立一个美好的爱情城堡。于大个子作为第二个男性暴戾地侵入他们之中,这就造成了马兆新对细草爱恋的断层状态,他无法忍受被于大个子奸污之后不完整的恋人。“我是个男人!是个男子汉!”他一直强调他的男性身份在爱情中的某种主导性的决定作用,在这种心理意识的驱使之下,他难以跳出固有的男性身份带给他的苦恼,他的爱情像梦一般消散在他所设定的理想模式之中。
马兆新是被历史抛向荒原的一颗失去方向的孤星,他渴望趋近细草这颗同样飘荡无依的星辰,却被于大个子这股狂风吹散向远方,支离的躯体与灵魂散落在荒原古道上,蔓延开来的只是零落的失却信仰的心灵。作为知青,他是被历史大潮框束的无法找到自身立足点的弱小个体;作为恋人,他又无力为所爱之人进行抗争更无法为自己的爱情给予宽厚的保护;作为理想信念的寻找者,他用被遮蔽的眼睛看向远方,最终也被远方放逐,留下一颗继续处在迷茫之中的心。
奥赛罗与马兆新在各自的境遇里背负着特定的身份与使命,他们相对于给他们设定身份的强者来说是卑微的存在,即使如奥赛罗一般英勇威武,也无法抵挡威尼斯人口中不屑的称呼,历史的抛掷也让马兆新失却了找寻信仰的方向。从他们同为男性这一身份与立场上看,二者都对理想、完美的爱情抱有诺大的期许,一旦意识到残缺的出现,甚至不惜在妒忌与恼怒中经受身心的毁灭。他们是执着而盲目的,又是卑弱而令人痛惋的理想人生的追寻者。
二、他者操控造成主体性的退避
奥赛罗和马兆新的身份意识使得他们在人生的历程中亦步亦趋,无奈彷徨。他们的心灵在徘徊与挣扎之中逐渐屈服于强势他者的压迫,亦即造成了他们主体意识在他者钳制下的退避。
在《奥赛罗》这部悲剧中,奥赛罗刚开始表现出审慎的冷静与值得骄傲的智慧,他因军事才能而受到贵族的重用,他因强烈的爱恋之情而勇敢地选择与苔丝狄蒙娜在一起,他有任用贤才的眼光与远见,这些都充分地体现出他的英勇气概。但在后来他对身旁伪装起来的“假好人”伊阿古的伪善与奸诈非但没有一点洞察,反而使自己完全地陷入后者的牵制与操控之中,他丧失了主动性而被伊阿古牵所引诱,进而酿成了杀妻自刎的悲惨结局。
奥赛罗自信于自己的赫赫战功给威尼斯政府带来的尊荣,他的身上自然的存在某些英雄主义的因子,他相信他在数次征战途中奇异凶险的经历和他无畏自由的精神感染了苔丝狄蒙娜,他和苔丝狄蒙娜的结合也让他感到无比幸福与满足。伊阿古的连环计却让奥赛罗幸福的心灵笼罩在了巨大的疑虑与纠葛之中,伊阿古在觊觎权力而不可得的情况下先是设计让凯西奥失去奥赛罗的信任,继而又让苔丝狄蒙娜误入不忠的境地,这一系列的事件是奥赛罗猝不及防的,他怀疑伊阿古所指控的人的时候却没有怀疑指控者言语的可信度,以至于在毫无防备之中走入了伊阿古设计的圈套,他在这个圈里画地为牢,自以为受到了爱情的欺惘,实则使苔丝狄蒙娜和凯西奥遭遇了更大的痛苦。他是无意间的受害者和不经意中的施害人,并在这种不经意与无意的交错之中造成了他者及自身的悲剧命运。
伊阿古在妒羡之中操纵了所有的剧中人物,奥赛罗、苔丝狄蒙娜、凯西奥和罗德利哥都受他的话语控制奔突在爱与恨之间。奥赛罗虽英勇善战,,但却在伊阿古的言语陷阱里丧失了判断力,丧失了自身的主体意识,“也许因为我生得黑丑,缺少绅士们温柔风雅的谈吐;也许因为我年纪老了点儿——虽然还不算顶老——所以她才会背叛我;我已经自取其辱,只好隔断对她这一段痴情。啊,结婚的烦恼!我们可以在名义上把这些可爱的人儿称为我们所有,却不能支配他们的爱憎喜恶! 我宁愿做一只蛤蟆,呼吸牢室中的浊气,也不愿占住了自己心爱之物的一角,让别人把它享用。”⑧在这样彻底的误解之中,他的理智与思考力被掩埋在了妒火与自鄙的情绪之中。“奥赛罗的欠考虑表现在偏狭、偏执以至于偏激上面”。⑨到后来即便没有伊阿古对他施加言语上的影响,他也难以控制他那脱了缰的愤恨与不满,在愤怒的诱使之下杀死了所爱之人。
奥赛罗用毁灭爱恋对象的方式试图湮灭妻子的不忠带给他的理想信念上残缺,由此他在苔丝狄蒙娜身上倾泻出强势的自我意识。他的主体性在伊阿古面前进行了无言的退让,反过来却在苔丝狄蒙娜这里反叛了这种退让,这样他的行为意识在挣扎与反叛中形成了悖论。躯体的毁灭和理想爱情的幻灭是相伴随而发生的,可以说奥赛罗对苔丝狄蒙娜的杀害从某种程度上来看是对自身完美英雄主义的一种保全,在一定意义上也是对自身主体性的一种残忍性的挽回。
马兆新在荒寂辽远的落马湖荒原上经历了三次归来与远去的彷徨历程:初次到落马湖的他是被历史选中的知识青年,出于对李天甜和苏家琪爱情的维护,在一次无妄的火灾中逃离了荒原;第二次他回到荒原时面对的却是细草要嫁给陌生男人,他在痛苦而愤怒中再次离开落马湖;当他第三次重访落马湖时他已完成了十五年的精神漂泊与自我流放,他在爬犁辙的延伸中将继续探寻在没有终点的信仰疆域里。
荒原上的马兆新是一个失去自我选择意识的人,历史车轮的旋转决定了他在荒原上的存在、离去与归来,于大个子的权威又一再造成他的退避、愤恨与怅惘。神秘寂寥的大荒原掩盖了他的青春理想,强势勇猛的于大个子湮灭了他美好的爱情,他在怯弱与彷徨中使自身的主体性遭到重重的压制,以至于奔波游荡在荒原与荒原外世界的夹缝中,在同一空间重复出现的时间流里丧失了信仰。
当我们透过马兆新关照到剧中的其他人物时,会发现这种主体性的丧失状态表现在每一个人的身上。李天甜和苏家琪在精神世界的共通与互溶是令人感动的,但他们无力去抗争加在自由爱情信念上的枷锁,在委曲求全中只能以放弃身体存在为代价来求取完美爱恋的存留;于大个子因自身婚姻的不幸与少时的惨痛经历而扭曲了本心,在落马湖王国用威权构筑了一个个牢笼去框束他者,最终也难逃悲戚的下场;毛毛就像荒原的女儿一般,她的身份造成她的无所依傍,一直在荒原上唱着悲凉的歌,这歌隐隐地预示着荒原上所有人人的命运——随风摇曳的生命,漂浮无依的心灵。
相对于其他人物的存在,我们在给予于大个子更多的关注时会发现,落马湖荒原对于大个子来说是天堂,是他一手经营起来的王国,他的所有行为都集中在给这个王国里的他人制造地狱般的悲哀与伤痛。他是其他人哀怅的施予者,可我们无可否认他也是那个时代的受害者,他因受过蔑视和伤害而拒绝强者对他的压迫,却在成为强者时却将伤害带给了更多弱小的人,最终在弱者对他的反叛中落得悲惨的下场。他是孤独的,只有黑子(于大个子的一只狗)和对妹妹的思念陪伴着他强势而纷乱、悲弱而迷离的心绪历程。
奥赛罗和马兆新先是在身份意识的笼罩下压抑自我的声音,继而在这种压抑的境遇里失去主体意识的判断与取舍,他们是值得同情的可怜之人,又是让我们心生可恨情绪的卑弱个体。但最终我们也不得不承认,他们的可恨之处定有令他们精神困顿的可悲之苦,由此他们的悲剧命运又是叫人可叹可哀的。
三、穷途与新生并置下的人生守望
《奥赛罗》和《荒原与人》虽然在写作时间上相隔近四百年的时间,但我们在剧作的品读过程中无不感受到作为个体的人类在面对自然、他者和自身困境时的弱小与迷惘。奥赛罗和马兆新置身在重重的压制与困苦之中,他们对理想人生的追求与这种追求遭到阻隔时的心态表现出了惊人的相似之处,所以在身份意识的感受上同样地被他人或群体的话语所牵制,在强大的异己势力的排斥下走向了精神上的困顿以及在这种困顿中的自我惩罚。
奥赛罗凶险奇异的征战经历打动了苔丝狄蒙娜的心,他和她的结合使他脱离了患难的战争生活而走进了家庭的宁静与温暖之中,这是他人生的第一次转折。然而伊阿古的计谋却让他的人生在喜悦之中经历了一场悲痛的突转,他原以为的温暖在他满腹疑团的愤恨之中转化成了无情的抛弃与虚伪的敷衍,他坠落在伊阿古制造的言语陷阱里,苔丝狄蒙娜的“欺骗”与“背叛”纠葛在一起成为他精神上的穷途与困境。根据前两部部分的叙述,我们可以看出奥赛罗身上英雄主义的烙印,当他妒火满腹,被嫉恨冲昏了头脑的时候,他奔突在自己设想的心理斗争之中。他试图在穷途之中寻找出口,可当他看见苔丝狄蒙娜美丽精致的形象时越加把这种美丽与放荡的行为联系在一起,于是为了保全他英雄主义理想下的完美爱情,他只有毁灭了他心目中钟爱的形象以保全记忆中的那种美好,他宁愿用毁灭而不是残缺的方式去保有这一份向往。
当奥赛罗自以为在悲痛的抉择与残酷的行为中保全了他的英雄形象时,殊不知这种无畏的行动恰恰使他沦为“黑心的魔鬼”(爱米利娅语)。奥赛罗的悲剧正是在这一次又一次的突转之中产生的,他的生命历程经由了从伤痛向温情的转移,却在种种诱使中走向了怀疑与误杀的痛苦境地,他真正的悲哀正在于他以为毁灭妻子“不堪”的行为带给他的创伤之后会获得心灵上的解脱,命运却给他罩上了更为惨痛的阴影,他对妻子的杀害最终成为对他自己最严酷的惩罚。他的新生是无望的,他只有用结束生命的方式去彻底摧毁这种无望,留给生者深重的思考。
马兆新的惨痛人生也如奥赛罗一样,是内心的风暴与无奈的挣扎。当他走向荒原时他就被放置在了无边际的理想信念的寻求疆域,于大个子对细草的奸污使他的精神世界彻底崩塌,他想要成为细草身心上的唯一,但却被于大个子推向了疑虑与惶惑的绝境。囿于他自身有着强烈的自我意识与身份意识,在面对细草的时候他难以排除于大个子的影子带给他的影响,他对细草的复杂情绪掺杂在他的主体性与身份自觉与于大个子的无形较量之中。
马兆新的人生理想在与荒原、于大个子、细草的情感纠葛中慢慢失落,他始终无力跳脱出内心的羁绊,并在这种羁绊之中将自我无限倍地进行蜷曲与缩小,进而在于大个子式的压制下逃向远方。 “以马兆新为代表的知青对失落了的自我的寻找,及其重建理想世界的愿望的破灭,也有人在存在中的自由选择,以孤独的个人奋斗反抗社会的‘存在’意味。”⑩马兆新是一个纯粹意义上的流浪者,他的梦想遗失在落马湖荒原上,他的爱情埋葬在落马湖的茫茫雪原。他在落马湖上祈盼的美好爱情造成了他精神上的枷锁,无论是十五年前与于大个子的争斗与角逐,还是十五年精神流浪后的迷惘与困顿,他的一切拥有与失去都在落马湖荒原上经历了生与灭。他选择十五年的精神流浪,试图去寻找真正的家,可当他在十五年后归来时,深痛的悲哀依旧盘踞在他的心中,“我的家在哪儿?我有老婆,有儿子,可是……说!我的家在哪儿?在哪儿?”(十五年后的马兆新对十五年后的毛毛说的话)他依然无法使得他的心灵得到安放,他的精神向往永远地迷失在了落马湖与流浪之地之间狭长的地带中而难以寻找与获得。
“这两道辙沟没有起点,也看不到终端。……这两道辙沟,它们只能平行着错身而过,却永远不会再有交点……”(十五年后的马兆新再次离开落马湖时的独白)这是马兆新对荒原的又一次告别,也是他漂泊之途的再一次开启。寻找着总有希望,虽然有伤痛与困顿的交织,谁又能预言希望不会在彷徨与漫长的寻找之后探出曙光,“人活着就是为了弥补世界的残缺,是为了追求极度的完善。正因为如此,生活的残缺才有意义。实际上,极度的完善是不存在的,但人们还是在追求,在头脑里构筑一个又一个理想王国。”(十五年后的马兆新对十五年的马兆新说的话)
结语
《奥赛罗》和《荒原与人》在创作时间、背景、文化环境上都存在有很大的迥异,而我们却透过剧作看到了人物命运惊人的相似之处。奥赛罗和马兆新都是在环境的裹挟之中不得自由的人,他们对自我的理想人生充满期许,他们作为男性有共通的对于完美女性的诉求。他们一直在环境和他者的牵制中苦苦探求属于自我的身份与存在意义,期待主体性的张扬与坚守。从他们的悲剧人生,我们能够洞见他们共同的精神困境——永远无法摆脱的来自境遇与自身的束缚,这种束缚却从相反的层面上促使着继续探寻的不息脚步。他们的生命历程是壮美而悲戚的,这种壮美与悲戚恰是对苦乐交织的矛盾人生的最好诠释。
注释:
① ③ ⑤ ⑧[英]威廉·莎士比亚《罗密欧与朱丽叶》[M].朱生豪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11.
② 李毅《奥赛罗的文化认同》[J].外国文学评论,1998年第2期:115—119.
④袁素华《爱情不能承受之重:奥赛罗的悲剧》[J].经典重释,2008年第5期安徽文学:178—179.
⑥臧保云《一代人的荒原——李龙云‘知青’话剧简论》[J].戏剧文学,2015年第12期.
⑦李龙云《荒原与人 李龙云剧作选》[M].北京市: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11月:8.
⑨罗益民《试论奥赛罗的性格系统》[J].外国语言文学研究, 2001年6月,第1卷第1期:79—87.
⑩马宏柏 生命意识· 存在意义·诗剧品格——略论李龙云《洒满月光的荒原》的创新追求河南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2年第29卷第6期.
参考文献:
① [英]威廉·莎士比亚《罗密欧与朱丽叶》[M].朱生豪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11.
② 李龙云《荒原与人 李龙云剧作选》[M].北京市: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11.
③ 詹俊峰,洪文慧 ,刘岩编著《男性身份研究读本》[C].武汉大学出版社,2010.9:425—429.
④ [丹] 扎哈维《主体性和自身性——对第一人称视角的探究》(哲学的转向:语言与实践译丛)[M].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4.
⑤ 谷海慧《从自我认同到欲望放纵——上世纪80年代与90年代话剧精神价值比较》[J].戏剧文学,2008年第1期:39—53.
 最新评论
最新评论|
版权所有© 中外文学研究课题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