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版权所有© 中外文学研究课题组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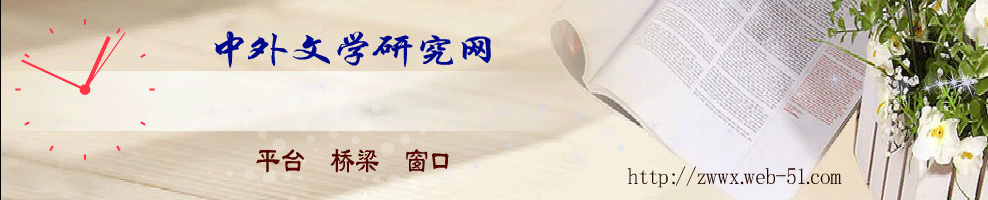
——黑娃和葛利高里形象比较
【内容摘要】长篇小说《白鹿原》中的黑娃与《静静的顿河》中的葛利高里这两个人物形象,既有着相似的经历和相同的悲剧性结局,又具有不同的个性特征。造成这种异同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但其最深层的根源,还是与他们所处的大体相同的时代和不同民族传统的伦理道德与文化氛围这种典型环境分不开的。
【关键词】民族性格 悲剧人生 黑娃 葛利高里 人物形象 文化氛围
【中图法分类号】I106.4
收稿日期:
陈忠实的长篇小说《白鹿原》以广博深厚的历史内容,跌宕起伏的故事情节,复杂多变的人物命运及色彩浓烈的风土人情,显示着现实主义强大的生命力,将其誉为史诗性作品是当之无愧的。读过这部作品,使人自然联想起同样被誉为史诗性作品的肖洛霍夫的长篇小说《静静的顿河》。本文无意对两部巨著作全面评论,仅试图从对其中两位重要人物形象的比较分析入手,陈述一己之见。《白鹿原》中的黑娃(鹿兆谦)和《静静的顿河》中的葛利高里这两个人物形象所经历的人生道路是十分相似的。当革命的洪流来临时,他们和千百万劳动群众一样都不可避免地卷入其中,因此,他们的人生之路有着普遍的社会意义。但是,这两个人物形象的独特的思想和艺术价值,恰恰在于在人生的旅途上,他们走着与众不同的艰难曲折的道路。当革命浪潮涌来时,他们都是最早的觉醒者,然而由于主客观方面的种种原因,使他们在革命与反革命阵营之间摇摆、徘徊和追寻,在积极与兴奋、孤独与彷徨、困惑与迷惘这样一些复杂思想情绪的伴随下,最终走向悲剧性结局。黑娃和葛利高里都出身于普通的农民家庭,如果不是赶上革命时代,他们都会如同祖辈那样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循规蹈矩地度过极其平凡的一生。然而,革命的洪流不仅带来时代的剧烈变化,也从根本上改变了他们的人生道路,为他们提供了充分发展个性、施展才能的机遇,他们就这样走上了人生舞台。
在《静静的顿河》中,作者以大量篇幅来表现葛利高里热爱生活、追求自由的性格特征。首先从对哥萨克传统习俗的描写来揭示主人公性格形成的客观原因。葛利高里无疑是一个杰出的哥萨克,他生长在顿河边上一个哥萨克大家庭里,从父辈那里继承了传统的群体性格,同时又具有独立不羁的气质和刚直孤傲的秉性。这种独特的气质和秉性使他并不满足于这样平庸守旧的生活而向往更加广阔的自由天地。因此,他虽然和他的父兄一样,恪守着哥萨克的传统道德和习俗,为了维护哥萨克的荣誉,体现哥萨克的勇猛、强悍而毅然去当兵打仗,但他并不是一个头脑简单的盲从者,而是一个有个性、有理想、有追求和富有正义感的哥萨克。他对所闻所见的事都要经过独立思考作出判断,从不随波逐流。为了哥萨克的荣誉,他去当兵打仗。战争在给他带来荣誉的同时,也带来了困惑。在战场上的第一次杀人,使他善良的心灵背上了沉重的负担,他对战争的最初反感是基于生命意识、生存本能和人道主义思想。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和布尔什维克的宣传,他原先的信念逐渐动摇,从对战争的怀疑和反感上升到理性的高度,思索着“为什么哥萨克背井离乡?为什么人们无冤无仇却互相残杀”这些重要的人生问题,从而自觉与不自觉地寻觅自己的人生道路。十月革命的胜利在葛利高里心中点燃了希望之火,在村里他最先参加红军,并因战功卓著升为连长。从此,他企盼着走上一条新的人生之路。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和他的所见所闻,使他对眼前的道路又产生了怀疑。在他看来,为人民谋利益的红军应该与白军完全不同,这也是他脱离白军参加红军的主要原因之一。于是,残酷的现实动摇了他刚刚建立起来的信念。眼前的一切使他失望,滥杀已经缴械投降的俘虏在他看来是极不人道的,他珍惜生命的意识和热爱生活的秉性受到沉重的打击。后来,在他负伤回家休养期间,布尔什维克在建立苏维埃政权过程中的一些过火行为和错误做法,激起哥萨克的反感并被白军利用而发动暴乱时,他也被卷入其中。葛利高里第二次参加白军固然不能排除主观原因,但主要是由于客观环境造成的。布尔什维克在顿河地区建立起苏维埃政权,但是新政权当时并没有给哥萨克带来什么好处,他们仍然生活在压迫之下。一些红军士兵随意抢劫哥萨克的财物,侮辱哥萨克的妇女……这样的现实是追求理想生活的葛利高里所不能容忍的,所以,他又抛弃了对苏维埃政权的认识和希望。但由于独特的秉性和特殊经历,在白军中也得不到信任和重用。后来,随着叛军的溃败,他再次看清了跟着他们走下去是没有什么前途的。所以,他反戈一击又参加了红军。虽然小说对他的这次转变缺乏必要的交代,但葛利高里第二次参加红军并不是一种投机行为,作品中写道:“自从参加了红军,他就变得精神愉快……”并且表示一直要干到能把过去的罪过都赎过来才算完。他努力这样去做,并因战功卓著而受到上级的嘉奖。我们不妨这样设想,如果不是被怀疑而复员,葛利高里也许就此会成长为一个优秀的红军指挥员。然而,也是因为他在白军和红军中来回摇摆的特殊经历和刚直孤傲的秉性,使他在红军中最终也得不到信任,被迫复员回家,在他心里刚刚点燃的希望之火又熄灭了。这时的葛利高里像一片孤独的漂蓬无所依附,对政治已心灰意冷,只希望能与家人过平静的农家生活。但是,此时他已身不由己,就连这一点小小的愿望也难以实现。回家后,他的妹夫、村苏维埃主席诃晒沃依逼他去登记,后又带人去抓他,使他仓皇出逃。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一个偶然的机会使他又暂时投靠了佛明匪帮,以便能有一个栖身之所。但他清楚地认识到这里不是长久的安身之地,同时也对自己的行为深深地自责,说明他的善良的天性并没有泯灭。他思念亲人,又不敢回家,暗中等待时机脱离佛明匪帮,计划带着阿克西尼娅到远离家乡的南方去度过这个混乱的年代。然而命运之神却总是捉弄他,可怜的阿克西尼娅在出逃的途中惨死在他的怀抱里,这对他又是一个致命的打击,几乎粉碎了他的生活信念。但尽管如此,葛利高里并没有彻底绝望,他仍然要顽强地生活下去,不管等待着他的将是什么命运。因此,他不顾一切地回到了使他又爱又怕的家乡。正如肖洛霍夫在同一位评论家谈话时所说的那样:“麦列霍夫返回故土!他仍然有着一颗活生生的心灵。这里面表现了他的力量!”这些描写充分展示了葛利高里顽强的生命意识和执著的追寻精神,同时也启发人们去思考造成他悲剧的原因。葛利高里形象之所以具有巨大的艺术魅力,其根本原因也正在这里。
《白鹿原》中的黑娃,在人生的旅途上走着一条与葛利高里既十分相似又不完全相同的道路。作品首先也是集中描写黑娃那种自幼形成的倔强的性格特征和桀骜不驯的精神气质。如族长白嘉轩出钱资助他去念书,而黑娃却不耐烦地说:“干脆还是叫我去割草。”当鹿兆鹏出于好意给他冰糖和点心时,不仅没有使他产生丝毫的感激之情,反而激起他的自卑和抵触心理。黑娃不愿走父辈的老路,要按照自己的设想和希望去生活。离开家乡到渭北平原当长工,尽管还是过着受剥削的日子,但对他来说这毕竟是按照自己的意志做出的选择。这些描写使黑娃性格气质中独立不羁的特点得到最初的展示,为他以后的行动奠定了基础。所以,当鹿兆鹏在白鹿原上掀起“风搅雪”的革命风暴时,黑娃成为第一个积极的参加者也就不足为奇了。他是一个普通的农民,又有着特殊的性格。在他幼小的心灵中早就播下了反抗的种子,萌发了叛逆的精神。随着革命的发展,黑娃也逐渐地显示了他的独特生存价值。在军阀混战的年代,他在鹿兆鹏的启发下放火烧了军阀的粮库,紧接着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又成为白鹿原上农协会的骨干,以极大的热情参与了革命活动。然而,政治风云的变幻使黑娃的革命热情受到了致命打击。但他既没有像他的一些兄弟那样屈膝投降,也没有像另外一些兄弟那样血洒白鹿原,而是走上了一条独特、漫长的道路。在逃出白鹿原后,经鹿兆鹏的引荐他加入了革命军队,并因才能出众而颇受器重。但是好景不长,由于革命与反革命势力的悬殊,他所在的部队在一次战斗中全军覆没。至此,黑娃那由自发的反抗意识发展而成的自觉的革命信念又一次遭到沉重打击,这也是他人生旅途上的第一个转折点。在此之前,黑娃的行动中显示着与葛利高里相似的性格。但黑娃毕竟是一个在中国传统文化的氛围中长大的农家子弟,如果说在此之前他主要是以一种积极、主动的态度来反抗压迫的话,那么在以后则主要是以一种消极、被动的态度来反抗的。传统文化的负面影响开始在他的头脑中产生作用。也是一个偶然的机会,黑娃落入土匪手中,面对生存的困境和匪首的诱骗,走投无路的黑娃思前想后,以痛哭一场的方式告别了过去,留在了土匪之中。此时的黑娃对政治已心灰意冷,只求能在乱世中保全性命。所以,后来当鹿兆鹏和白孝文各自代表游击队和保安团多次前来游说、劝降时,他都不为之所动,企图在国、共两党之间寻找一条中间道路。黑娃的这种选择是其自身性格发展的必然归宿,他毕竟是一个普通农民,对革命的最初认识和理解,其实与土匪们的劫富济贫并无多大区别。这种思想早在“五四”时期鲁迅的小说中就已得到深刻揭示。明白了这个道理似乎也就找到了黑娃能够长期栖身于土匪之中的深层原因。然而,问题并没有这么简单,对黑娃的思想行为最具有影响的因素,还应该说是传统文化的氛围。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传统文化具有较大的保守性,它倡导的是对现存制度的修补和维护而不是背叛和超越。因此,黑娃的入匪还不是他的最后归宿,在传统文化的影响下,他最终还是率众接受了代表现行制度的保安团的招安和改编,由一个现存制度的叛逆者变成一个维护者,这是黑娃人生之路的第二次转折。从实质上来说,黑娃的反抗道路最终也没有能够跳出传统的农民起义的模式,走着一条造反—招安的传统之路。而黑娃形象更深刻的蕴含还在于在儒家文化的感召下,他在精神上向传统的彻底皈依。此后,他也的确做了许多“好事”,如带头戒烟,整顿军纪等,从而名声大振。在黑娃“悔过自新”的过程中,最重要的两件事是拜
在人的一生中,爱情、婚姻是与事业并重的主题,在婚恋问题上也反映着黑娃与葛利高里相似而又相异的态度和经历,折射出文化传统和民族性格的差异。葛利高里向往、追求真正的爱情生活,他不顾父亲的言语奉劝和棍棒警告,勇敢地与阿克西尼娅相爱,向哥萨克传统伦理道德提出挑战,带着心上人远走他乡,摆脱家庭的束缚去追求真正的爱情生活,为此付出了巨大代价。葛利高里的这一举动在十月革命前后的哥萨克社会中,也是惊世骇俗之举,必然受到众人的指责。在麦列霍夫大家庭里,脾气暴躁的父亲具有绝对的权威,他是哥萨克传统伦理道德的维护者和传统生活方式的体现者。因此,葛利高里离家出走具有双重意义,它不仅是对传统生活方式的有力反抗,也是对传统伦理道德的大胆背叛,这是他在追求新生活的道路上迈出的坚实的一步。在葛利高里看来,婚姻必须以爱情为基础,因此在爱情、婚姻问题上他注重感情因素,而不仅仅是满足于生理需求和传宗接代的婚姻形式。同时,爱情、婚姻又是人生中最具有个人色彩的内容而不必求得他人的认同,只要自己感到幸福就算达到了目的。在爱情、婚姻问题上,黑娃与葛利高里的态度和行为的异同也是很明显的。黑娃外出扛长工时,在雇主郭财东的小妾小娥的引诱下萌发的性意识,最终升华为炽烈的感情,经过一番周折,他带着小娥回到家乡。这是黑娃在新的生活道路上迈出的有力的一步,也是他独特性格的鲜明展现。这一惊人之举在白鹿村里引起极大震动,白鹿原上最具革命性的人物鹿兆鹏也因自己难以做到婚姻自主而对黑娃大加赞赏,称他“是白鹿村头一个冲破封建枷锁实行婚姻自主的人”。但在现代中国农村这样一个以宗法关系为基础的社会中,个人的婚姻被纳入家族的群体之中,根本没有自主的权利。所以,在白鹿村这样一个典型的宗法家族的众人眼中,黑娃在婚恋上的行为是大逆不道的。尽管他以自己切实的行动向传统伦理道德提出了勇敢的挑战,然而,由于行动主体置身于浓厚的传统文化的氛围之中,这种挑战是软弱无力的。黑娃无法从根本上彻底背叛传统,为了使他和小娥的婚姻关系能够持续下去就必须使之“合法化”,赋予它一个名正言顺的形式。因此,当黑娃在异乡自主娶了小娥后,必须回乡认祖归宗,以求得家族的认可和接纳。不幸的是他的抉择一开始就是悲剧性的,宗法伦理的巨网笼罩着中国农村的每一个角落,它绝不会承认和接纳小娥这样一个女人,所以不论回乡与否,黑娃与小娥的婚恋结局都将是一场悲剧。黑娃接受招安后携新妻回乡祭祖之举,则从另一个角度再次说明了这个问题。从以上的分析对比中我们可以看出,葛利高里与阿克西尼娅的恋爱关系中充分体现着西方民族的文化传统和性格特征。当家庭成为追求自由、幸福的羁绊时,可以将它踢开而不必顾及后果。而在黑娃和小娥的婚恋关系中却充分反映了华夏民族的文化传统特征。当婚姻与家庭及其伦理道德发生冲突时,就必须放弃个人的选择以维护家族的荣誉,否则就只有走向毁灭的结局。葛利高里和黑娃在对待婚恋问题的主体态度和行为中,也显示着传统文化与民族性格的差异。哥萨克社会虽然带有保守、落后的封建色彩,但它毕竟是西方民族大家庭中的成员,体现着西方民族某些传统的优良品质,如酷爱自由、追求平等。因此,尽管哥萨克社会也是一个以男性为中心的社会,但它对妇女的压迫和束缚远没有中国宗法制的农村那么严酷和牢固,而给予她们一定的自由平等的权利。
《静静的顿河》对女性形象的描写都不同程度地反映着这个特点,而这个特点在葛利高里对阿克西尼娅的态度中得到最为鲜明的体现。在葛利高里和阿克西尼娅的恋爱过程中也出现过一些误解和挫折,但是葛利高里对阿克西尼娅的爱是矢志不移和真诚平等的,从未因外界的干扰而产生动摇,表现出他对爱情的执著与主动。阿克西尼娅最终死在葛利高里的怀抱里,足以显示出他们之间至死不渝的爱情。与阿克西尼娅相比,小娥是十分不幸的。黑娃和小娥虽然也产生了爱情,但却带有浓厚的宗法伦理色彩。在描写爱情的中国传统文学中,女性大多处在主动的位置而男性则往往是被动的。在黑娃与小娥的关系中也突出地反映着这个特点。黑娃和小娥在患难中孕育了炽烈的感情,但后来随着政治风云和个人生活的变化,男性在婚恋中的软弱、被动的特点在黑娃身上得到明显的体现。当黑娃从白鹿村逃走时,小娥哭喊着要跟他一起走,黑娃却拒绝了她。传统文化的熏陶使黑娃性格中自私、软弱和被动的一面在关键时刻暴露得淋漓尽致,只顾自己逃命而不顾情人的死活。后来,当黑娃得知小娥惨死的消息时,立即寻查凶手,这固然是为小娥报仇,但也是出于对自己荣誉的维护。随着岁月的流失、环境的改变,黑娃的复仇念头逐渐淡漠,直至消失。此时的黑娃已从心中把小娥彻底抛弃,所以最终能与杀害小娥的凶手——自己的父亲和解,在爱情与家族之间他选择了后者。因此,从实质上来说,黑娃对小娥的恋爱最终也没有能够超出始乱终弃的传统文学模式。从葛利高里和黑娃的婚恋经历所导致的社会反应来看,也表现着传统文化的差异和民族心态的不同。对于葛利高里与阿克西尼娅的恋情以及离家出走的举动,虽然在鞑靼村引起一定的震动,但很快就平静下来。潘苔莱也没有因此与葛利高里剑拔弩张,断绝父子关系。相反,随着时间的推移禁不住思子之情,终于借送入伍装备之机前去看望儿子,并且对葛利高里与阿克西尼娅非婚生的孩子予以认可。小说描写他一本正经地审视了在一堆破布片里伸出的小黑脑袋后,很自豪地说:“是我们家的血统……”从他对阿克西尼娅态度的转变中也许更能说明问题。当他因儿子与阿克西尼娅偷情被人们当众嘲笑、羞辱后,气急败坏地到阿克西尼娅家里兴师问罪,警告她不许勾引葛利高里。可是当他领教了阿克西尼娅的疾风暴雨似的回击之后,像只斗败了的公鸡,垂头丧气地一瘸一拐走回家去。后来在给儿子送装备时他又见到了阿克西尼娅,开始对她态度冷淡,但逐渐变得热情起来。这些描写都足以说明以潘苔莱为代表的传统伦理道德不堪一击,也反映出哥萨克社会对葛利高里和阿克西尼娅叛逆行为无可奈何的心态。对他们的叛逆行为的无奈和默许,显示着哥萨克文化传统和民族心态的两面性:既维护传统伦理道德,又认可自由、独立的人格追求。然而,黑娃和小娥对婚恋的自主抉择却演出了一幕惨烈的人间悲剧。以儒家文化为精神支柱和行为准则的白、鹿家族,对任何离经叛道的行为都是绝对不能容忍的。当黑娃从外乡带回来一个漂亮女人59做媳妇时,白、鹿家族最初的反应是震惊和疑惑,在弄清了真相后毫不迟疑地让黑娃赶快把她赶走。如果说白、鹿家族对黑娃的“过失”还希望他迷途知返而给予暂时宽容的话,那么它是绝对不能容忍和接纳小娥这样一个“不贞洁”的女人的。因此,尽管黑娃和小娥也奋起反抗,但是从此就陷入了痛苦的深渊。他们的反抗是软弱无力的,等待着他们的只能是悲剧性的结局。从白、鹿家族的家长们对待小娥的态度上,也许更能反映儒家文化的惰性和传统伦理的“吃人”本质。从根本上来说,白、鹿家族的家长们对小娥的态度都是相同的,他们剥夺了这个柔弱女子追求自由、幸福、甚至起码的生存权利,但每个人的具体做法又有区别,显示着他们不同的性格和身份以及传统文化的巨大威慑力。黑娃的父亲鹿三对小娥这个不合名份的儿媳深恶痛绝,视为祸害而根本不予承认,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并最终残忍地杀害了小娥。这些描写十分符合一个受传统伦理观念熏染很深的普通农民的思想行为。而鹿子霖对小娥的态度和行为,则反映出他狡猾、阴险、无耻和趁人之危的性格特点与依仗权势的身份地位。他既以小娥的美貌来满足无耻的淫欲,又将她作为同白家明争暗斗的工具。白嘉轩则与众不同,他貌似平和宽厚的态度和行为却是极有威慑力的。在白、鹿家族中,他可以说是宗法伦理的正统代表。他对小娥这样一个“下贱”女人的厌恶之情不亚于任何人,但他并没有也不屑于对她施以肉体上的欺凌,而是对她进行精神折磨和灵魂的奴役。活着不让她进祠堂,死了让她下地狱,还在她的骨灰上修盖镇邪塔,让她永世不得翻身。如果说鹿子霖的淫欲只能使小娥感到屈辱和悔恨,鹿三的利刃使她的痛苦彻底解脱,那么,白嘉轩的精神枷锁则牢牢地套在了她和白鹿村村民的心灵上而永远不能解脱。对于在传统宗法伦理束缚下生活的村民们来说,难道还有比这更令人心灵震颤的惩罚吗?
从以上分析来看,把《白鹿原》对黑娃形象的塑造与《静静的顿河》对葛利高里形象的塑造相比较,虽然还缺乏细腻的性格刻画和必要的心理描写,但黑娃形象的悲剧性命运是他性格发展的必然归宿。人物行为貌似偶然,实则包含着必然,黑娃的悲剧是他对传统从反抗到皈依的必然结果。当然,《白鹿原》对人物形象的描写、刻画的确没有《静静的顿河》那么细腻、明了,但正是在这些方面又显示着陈忠实凝炼、含蓄的风格。不同的读者对葛利高里和黑娃形象的认识和理解不同,从接受美学的角度来看是十分自然的。我以为不论是在对人物独特的民族性格的展示和悲剧性命运的美学意蕴的张扬上,还是对人物性格的丰富性和复杂性的描写和刻画上,黑娃的形象都足以与葛利高里形象相媲美。两位性格相近、民族文化传统相异的人物在动荡的年代走着相似的人生之路。以存在主义观点来看,他们都试图把自在的存在变为自为的存在,以展示自己独特的生命价值和生存意义。但是,生活在不同文化传统的氛围中,他们的性格和经历也必然会打上民族的印记。他们悲剧性命运的形成都有着主客观方面的原因,但又各有侧重。概括地说,葛利高里的性格中体现着西方民族自由、奔放的特点,行动中表现出更多的积极、主动性,造成他的悲剧的原因更多的是外在的环境。而黑娃由于受以保守、封闭的儒家文化为基础的民族性格的熏陶,在行动中表现出更多的消极和被动性,造成他的悲剧的原因更多的在于内在的性格。
 最新评论
最新评论|
版权所有© 中外文学研究课题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