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版权所有© 中外文学研究课题组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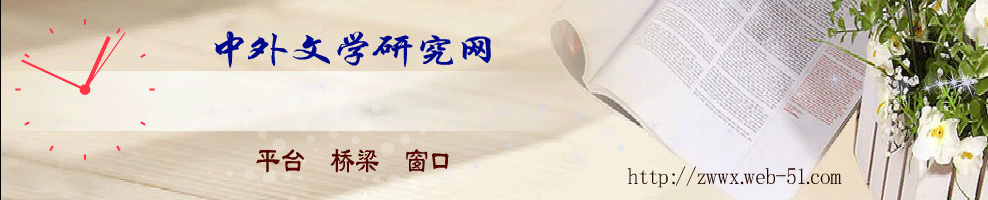
|
盛宁 | ||
20世纪的60年代,是全世界范围内的一个矛盾冲突激化期。且不说笼罩整个东西方的冷战阴霾和在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各国风起云涌的反帝、反殖民族解放运动,即使在欧美发达资本主义各国的内部,社会政治、经济、种族矛盾所引发的激烈冲突也是彼伏此起,一浪高过一浪。今天,不少的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都趋向于把60年代看成是对50年代的一种反动或断裂,其“标识”就是“政治和文化上的激进主义”(丹尼尔·贝尔语)。 | ||
|
稿件来源:中华读书报 |
 最新评论
最新评论|
版权所有© 中外文学研究课题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