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版权所有© 中外文学研究课题组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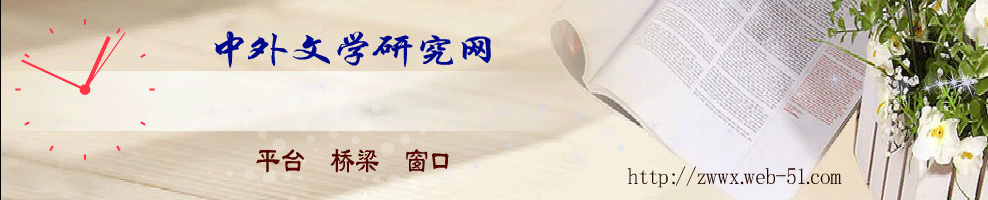
学校:西北师范大学 专业: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 姓名:蔡静
摘要:《日瓦戈医生》是苏联著名作家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的代表作品,整部作品的创作历时十年。作品主要展现的是20世纪初到卫国战争期间俄罗斯知识分子的广阔生活图景,小说不仅涉及到生与死的秘密、俄罗斯历史、革命、知识分子、基督教等问题,更为我们呈现出俄罗斯民族所具有的优秀精神品质。本文主要从小说中的人物形象、故事情节及意象等三个方面进行研究,试图对小说中所蕴含的宗教因素进行浅要分析。
关键词:《日瓦戈医生》;帕斯捷尔纳克;宗教
在20世纪的文学史上,帕斯捷尔纳克是个说不尽的秘密。他1890年2月10日生于莫斯科一个特殊的犹太家庭,是一名犹太教哈西德派的信徒。他从小受到多方面的艺术熏陶。作为诗人,他早在20世纪初就蜚声文坛,30年代被苏共“党内头号思想家”布哈林称为“我们当代诗歌界的巨匠”;作为小说家,他创作的长篇小说《日瓦戈医生》反应了俄罗斯近半个世纪的社会风貌,曾获1958年的诺贝尔文学奖。
有关《日瓦戈医生》中宗教问题分析、探讨的论文很多,主要可分为三个方面,即:对小说中人物形象的宗教原型分析(主要集中在日瓦戈与拉拉的形象研究上);对小说中“死亡”“复活”主题的研究;对小说诗歌文本与散文文本的宗教互文性研究等。帕斯捷尔纳克曾说:“我想在其中提供近45年间俄罗斯的历史映像,……作品将表达对于艺术、对于福音书、对于在历史之中的人的生活以及许多其他问题的看法……这个作品的氛围是我的基督教。”【1】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他也曾断言《日瓦戈医生》“在全世界仅次于圣经,排在第二位。”【2】由此可见,作者对这部小说所涉及的宗教现象是尤为重视的,对我们研究其中的宗教因素也给予了一定程度的价值肯定。
在分析这部作品之前,笔者认为我们有必要搞清一个事实,那就是:这部小说的作者帕斯捷尔纳克不是一位基督徒,而是一位犹太教哈西德教派的信徒。并且,据他的妻子吉娜依达回忆:“尽管他爱读圣经,会背诵圣诗,赞赏圣诗中含有的高尚道德和优美诗意,但从不去教堂。他把宇宙观视为最高起源,并把大自然奉为某种永恒和不朽的东西。从一般通常的意义说来,他并不信奉宗教。”【3】另外,他身处俄罗斯,势必会受到当时俄罗斯国内盛行的基督教东正教的影响。
所以,笔者认为,我们不应仅因为作品中涉及许多有关《圣经·福音书》中的内容以及作者曾向外界宣称的“这个作品的氛围是我的基督教”,就认为作者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徒,并将这一论断作为依据拿来分析这部作品;同时,无论是哈西德教亦或是基督教,它们对于作者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更多是有机地存在于帕斯捷尔纳克头脑中思想的投射”【4】,因此,这部作品并非那种生硬的、纯粹为表现宗教而创作的作品(如《十日谈》或《坎特伯雷故事集》那般),哈西德教、基督东正教的影响已经溶入作者的血液、灵魂中,在他无意识地创作中会自然地流露于字里行间。搞清这一事实后,我们下面来具体分析一下作品中的宗教因素。
一、 人物形象体现的宗教因素
(一)人物形象的宗教原型
1.日瓦戈形象的宗教原型。
现今有关日瓦戈形象的原型分析主要有以下三种观点:“多余人”形象、“耶稣基督形象”、俄国非主流文化中的圣愚。受大家普遍认同的看法是第二种,即认为日瓦戈的形象与《圣经》中的“耶稣基督形象”相互对应,他们都担负着“拯救人生命、提升人灵魂”的使命。对此种看法笔者不反对,但笔者认为,在日瓦戈的身上也有一些哈西德派的影子。哈西德派是一种东欧犹太教存在主义——神秘主义运动,其信徒备受压迫,受尽苦难,因而从情感上认同宣传快乐地认识上帝,信徒们应当以自己充满感激乐观的心灵接受上帝。他们主张以一种快乐的让普通人得到精神慰藉;认为上帝无所不在,对神虔敬比作学问来得重要;反抗严格的律法主义和律法学术。【5】
从拯救人的生命来看,作为一名医术高明的医生,无论在战前医院还是在野战医院,抑或是逃往瓦雷金诺以及最后在拉拉离开后的生活中,他一直履行着治病救人的职责。如在他们全家移居瓦雷金诺的时候,在谢肉节的那天他在经历了一系列内心挣扎之后救治了一位有病的农夫;又如在白军与红军的一次交战中,他秘密地救治了一名白军士兵。他一直履行着作为一名医生所应具备的治病救人的职责,这与《圣经·福音书》中耶稣基督使人们脱离病痛的故事正好契合。
从提升人的灵魂而言,他不仅解决人们的肉体病痛,同时,也给予人们一定的精神慰藉与思想上的帮助。如在他的岳母安娜·伊万诺夫娜得了肺病临死前,为了安慰她,使她抛却死亡带来的精神苦痛,他告诉她说:“死亡是不存在的,它和我们无缘。”“圣徒约翰说过,死亡是不会有的,但你接受他的论据过于轻易了。死亡之所以不会有,是因为先前的已经过去。……如今要求的是崭新的,而崭新的就是永恒的生命。”【6】这里,日瓦戈身上既隐约体现了哈西德教义中“以一种快乐的崇拜方式让普通人得到精神慰藉”的主张,又具有基督教“解救人灵魂”的特点;又如在拉拉说“我是个被毁了人,一生都带着受伤的裂痕。我是个过早地被人变成了妇人,早的简直是罪恶,把生活最糟的那一面朝向了我”【7】时,对此,他的回答是“我来得太晚了,为此我难过得近乎绝望,当时没有能同你在一起,否则我就会阻止发生这种事,不让你受苦”【8】。在此,体现了他基督教“博爱、宽恕”的思想。再如日瓦戈在他的诗作中说,“我几乎为所有人担忧,仿佛他们的骨肉。我愿像雪一样融化,像这清晨紧缩眉头”【9】,他如耶稣基督一般,身体力行着基督博爱、宽恕的精神,在苦难中实现自我灵魂的提升、超越。
此外,日瓦戈对于政委金茨的政治言论“感到难为情”、“希望能远远地离开这些平庸的高调和言之无物的陈词滥调”【10】,这一点也反映了日瓦戈身上具有的“反对严格的律法学术/主义”的哈西德教观点。
2.拉拉形象的宗教原型。
一般认为拉拉形象的宗教原型是抹大拉的马利亚。作为日瓦戈所钟爱的女性,她集外在与内在美于一身,是如女神一样存在的人物。她同日瓦戈一样饱尝生活的苦厄、艰辛,少女时曾受科马洛夫斯基的诱惑而失足,落入罪恶的泥淖,受尽屈辱;婚后又被丈夫安季波夫离弃;好不容易遇上精神伴侣日瓦戈,却因时势不稳,又被推向了魔鬼科马洛夫斯基。她的一生是忏悔的一生,虽然她“并不信奉宗教,也不相信那些教堂仪式。但为了承受生活的重压,有时也需要某种内在音乐的陪伴。这种音乐并不是每一次都能自己谱写的。它是上帝关于生命的箴言,拉拉到教堂正是去哭它。”【11】她独自去教堂替自己和奥莉娅忏悔: “祝福吧,心灵空虚的人,祝福吧,痛哭失声的人,祝福吧,渴望并追求真理的人。”【12】我们可以从拉拉坎坷的世俗人生中看到她精神神圣性的一面,她虽非宗教信徒,但她却深深的懂得宗教精神的真谛。她要以平凡生活的“常道”来验证伟大基督精神的“常理”,以人世间的真善美行为实现灵魂在天国的永恒。日瓦戈说,“我不爱没有过失、未曾失足或跌过跤的人。她们的美德没有生气,价值不高。生命从未向她们展现过美。”【13】的确,拉拉是真实、善良、美丽的,她尽管失足却仍保持着灵魂的圣洁,这正符合圣洁的圣母玛利亚形象。
(二)人物形象中的宗教传道者
1.传道者之一——韦杰尼亚平。
韦杰尼亚平是一位被革出教门的神甫,是小说主人公日瓦戈的舅父。他同“那些抱残守缺地信奉某些教条,满足于咬文嚼字,不求甚解”的“当代作家、教授和革命哲学家”不同,“他热心追求的思想,应该是可以鼓舞人的东西,在前进中如实地指明种种不同的道路,能使世间的一切趋于完善;……他渴求的是崭新的观念。”他是个“崇尚自由的人,对自己不习惯的东西不抱任何成见,”“怀着同一切人平等相处的高尚感情,”“对一切事一眼就能看穿,并且善于用最初想到的方式表达自己的思想”【14】。
他有着浓厚的基督教情怀,同时,也具有一些哈西德派的特点。他是日瓦戈的精神启蒙者,日瓦戈幼年起就深受他的影响。他曾对日瓦戈说: “任何一种组织起来的形式都是庸才的栖身之地,无论他信奉的是索洛维约夫,是康德,还是马克思。……世界上难道真有什么值得信仰的吗?这样的事物简直是凤毛麟角。我认为应该忠于不朽,这是对生命的另一个更强有力的称呼。要保持对不朽的忠诚,必须忠于基督! ”【15】此处,表现了哈西德派认为“对神虔敬比做学问来得重要”及“反抗严格律法主义和律法学术”的观点。他还讲到:“只是基督降生之后,时代和人类才自由地舒了一口气。只是在他以后,后代人的身上才开始有了生命,人不再死于路旁沟边,而是终老于自己的历史之中,死于为了战胜死亡而从事的火热的劳作之中,死在自己为之献身的这个主要任务之中。”【16】他认为,有了基督才有人类历史,才开始真正属于人的生活,因为只有耶稣降生之后人才找到了永生的途径,人才具有了个体的特征,人身上的个性才得以解放。他还主张没有武器的真理,用日常生活解释真理,他说:“福音书当中最重要的是伦理箴言和准则。我以为最要紧的是应该懂得,耶稣宣讲的时候往往使用生活中的寓言,用日常生活解释真理。”【17】在此也暗含了哈西德派“反抗严格律法主义和律法学术”的宗教思想。
他传达给日瓦戈的思想是,在基督身上,个性、不朽、神性是统一的,都是他生命力的体现。忠实于不朽就是忠实于基督,忠实于生命本身。他关注的是耶稣表现出的人的特性,并未把他当作高高在上的神来看待,他认为耶稣从一开始就是一种谦逊的形象,他的思想以及传道的方式也是相当人性化的,没有任何的强制性质,这是源于一种最朴素的爱的,与人平等对话、交流的关系,此处表现了哈西德派宣传“快乐的人是上帝”的主张。韦杰尼亚平的传道者形象在小说中具有重要意义,他是作为小说中日瓦戈强烈的宗教情怀的生命精神的持续回应,是主人公内心话语的另一种呈现方式。
2.传道者之二 ——西玛。
虔信宗教的西玛是韦杰尼亚平的崇拜者,民间朴素宗教思想的代表。拉拉常聆听这位思想深邃的智者讲述圣经,她可以说是小说中拉拉的精神启蒙者。她看似平凡的身上透露出一种不平凡。她曾对拉拉讲述抹大拉的马利亚:“她( 抹大拉的马利亚)乞求主道: ‘请解脱我的责任,像解开我的头发一样。’意思是说: ‘宽恕我的罪孽,就像我散开头发一样。’渴望宽恕和忏悔表达得多么具体! 手都可以触到。”“世界有所进展。罗马统治结束了,数量的权力结束了,以武器确定全体人口、全体居民生活的义务废弃了。领袖和民族已成过去,取而代之的是个性和对自由的宣传。”【18】
西玛的话语表明: 上帝珍视个体,崇尚私生活的日常,并且以个性为出发点评价世上的一切。她以“基督”、“上帝”等词语消解“领袖”、“民族”等概念,强调“生命”、“个性”、“日常”、“自由”在宇宙和神性世界中的重要性,它们甚至与上帝是平等的: “上帝和生命之间,上帝和个人之间,上帝和女人之间,多么接近,多么平等! ”【19】正因为如此,个人的生活才是神圣的,才能成为“充满宇宙空间的”,“上帝的纪事”。
二、 故事情节中的宗教因素
在这一部分,笔者主要想从小说情节中一个重要方面:拉拉的三段感情悲剧来分析小说故事情节中所体现的宗教因素。这三段感情悲剧包括:科马洛夫斯基与拉拉的感情悲剧;安季波夫与拉拉的感情悲剧以及日瓦戈与拉拉的感情悲剧。笔者认为,在这三段感情悲剧中,也鲜明体现了作者的宗教思想。下面,笔者将分别对这三段感情悲剧中存在的宗教思想进行详细分析。
(一)科马洛夫斯基与拉拉的感情悲剧
科马洛夫斯基是拉拉已故父亲的朋友,拉拉母亲的情人,最终也成为了拉拉的情人,他在拉拉17岁的时候将其引诱失贞。小说对二者的情欲没有进行细致描写,作者只是轻描淡写地提了一下科马洛夫斯基“挑逗起她心中渐渐苏醒的也想模仿一番的不良念头”的“那种暧昧而大胆的举动”,然后又描写了一下拉拉“在情欲的噩梦中越陷越深,但每当她清醒过来的时候吓得头发都竖立起来。但夜里的癫狂又像是巫术那样无法解释的矛盾。”【20】这种矛盾心理。相反,作者用了大量笔墨描写拉拉在被科马洛夫斯基引诱失贞后的心里挣扎与忏悔,“妈妈要是知道了,一定会打死她的。把她打死,自己再自杀。”“正像通常所说的,她已经是堕落的女人了,成了法国小说里的那种女人”“她双肩抖动,痛楚地哭着。”“一种刺心的沮丧和对自己的畏惧长久地留在她的心里,在那里扎下了根”【21】。 当涉世不深的她终于意识到科马罗夫斯基仅仅把她当作一个肉欲的、性感的、媚惑的玩偶时,她在痛苦的顺从与绝望中挣扎并想到了死。为了获得救赎,她一个不信奉宗教与宗教仪式的人,开始到教堂忏悔,期望获得心灵的皈依与灵魂的净化。笔者认为,这一点正体现了作者禁欲主义的立场、观点,他在小说中暗示人们在犯了违背基督教条例“纵欲”后,应忏悔反思自己的过错,不应纵欲。
另外,在小说中作者还重笔墨描写了拉拉拿着她弟弟的手枪准备报仇泄恨、杀死科马罗夫斯基的场景,她用超越自我的勇气向毁掉她青春的科马罗夫斯基举起了复仇的枪,“这是射向科马罗夫斯基、射向她自己、射向自己命运的一枪”;“她拼命挣扎,无时无刻不在反抗,一心要按自己的意志改变命运,开始全新的生活。”【22】。笔者认为,在此处科马洛夫斯基不仅是毁灭拉拉青春的罪人,更是人性“情欲”的化身。而拉拉此时要毁灭的不仅仅是科马洛夫斯基本人,更多的是要毁灭人性中罪恶的“情欲”。她将它看作是罪恶,看作是破坏、羁绊自己人生与生命的东西,因此,她要毁灭他。这一点可作为作者禁欲思想表达的一个小高潮。但是,这次复仇的结果是失败的,由此受骗上当的拉拉终生都未逃脱成为科马罗夫斯基情欲奴隶的厄运。
(二)安季波夫与拉拉的感情悲剧
拉拉与安季波夫的结合是为了摆脱科马罗夫斯基情欲的噩梦,步入正常的生活。拉拉师范专修毕业就迫不及待地嫁给同样奉自己为女神并苦苦追求自己的帕维尔·帕夫洛维奇·安季波夫。安季波夫是一个“对她喝水用的茶杯和她睡觉的枕头都感到嫉妒”“发狂爱着她”的人,迎娶拉拉是他梦寐以求的爱情理想。拉拉也相信安季波夫会原谅因无知而失身的她,企望通过婚姻的形式来庇护自己,实现捍卫做妻子及母亲的权利和尊严。但她万万没想到,安季波夫无法接受“在他之前她曾经属于别人”这个事实,并因此倍受煎熬和痛苦。他想到了离婚,想到了投河,最终他选择了抛弃拉拉和心爱的幼女,投身革命。由此,拉拉所期盼的美好婚姻之梦就这样被这位曾深爱她的男人打碎了。
安季波夫——这个曾爱她到发狂的男人,由于受到根深蒂固的俄罗斯东正教传统文化思想的影响,无法面对拉拉婚前不纯洁的真相,由此变得异常冷漠、乖僻。俄罗斯作为一个具有浓厚的东正教传统思想的国家,其宗教思想触及文化生活的各个领域,男尊女卑的思想在东正教教义中尤被强调,认为女性不仅要贞洁而且要做一个生儿育女,服侍丈夫,照顾家庭的好妻子,这是女性尊重“律法”的前提和重要表现。拉拉的所有努力都是为了丈夫,她千方百计去维系这来之不易的合法婚姻。而在安季波夫看来,拉拉失身于他人,不但触犯了男权主义的传统,也严重损害了他作为男人的尊严。因此,安季波夫最终选择了离开,而拉拉被抛出了婚姻生活的伦理秩序之外,沦为俄罗斯男权文化传统的牺牲品。在这段感情悲剧中,作者鲜明地呈现了东正教中“男尊女卑”的思想。
(三)日瓦戈与拉拉的感情悲剧
在帕斯捷尔纳克看来,日瓦戈与拉拉就像亚当和夏娃在世界创立之初那样相爱,这种爱象征着永恒的人性美,因为这种爱是源自人类最初的本能,他们的契合使彼此有一种美妙的精神上的满足感。但是他们的关系并不是合法的婚姻,他们的爱在宗教批判角度看来有着纵欲的成分,这也使他们时时怀有一种负罪感。日瓦戈医生从小就具有基督徒仁慈博爱的精神,崇尚自由、关爱人性的独立精神和批判意识及勿以暴抗暴的政治态度和人道主义理想,同拉拉的普世价值观引起了强烈共鸣,由此引发了彼此的爱情。他们忘情于尘世,自比亚当和夏娃,心有“属于整个宇宙的感觉”。他们相知相爱,彼此都认为找到了精神的支柱和爱的归宿,找到了自己美好的理想。拉拉甚至把日瓦戈医生当作自己的精神堡垒和生命支柱。然而,日瓦戈终究由于他的软弱、不敢负责、不敢担当,以及难以摆脱家庭和伦理道德的束缚,将拉拉推向了科马洛夫斯基,导致了不可挽回的爱情悲剧。
小说中有一段关于日瓦戈在瓦雷金诺准备与拉拉断绝关系的心理描写:“是背叛了她(指冬妮娅),还是看上了比她更好的人?不是,他没选别人,也不去比较。‘爱情自由’的思想和‘感情的权利和需要’之类的话,他是完全不能接受的。谈论或是盘算这些事他觉得都是低级趣味。在生活当中他没有摘取过‘随心所欲的花朵’,不把自己归入半神或者超人之类,不为自己要求优待和特权。在良心龌龊的重压之下,他已经疲惫不堪”【23】。此处表现出日瓦戈深受基督教禁欲思想的影响,不能接受“随心所欲”的爱情。
他们的爱情对当时传统的伦理道德提出了挑战,拉拉也为此陷入深深的矛盾与自责中,她曾坦言:“在这种粗野的、时刻戒备的柔情中孕育着某种孩子般不驯服的、不允许的东西。这是一种任性的、毁灭的本能,同家庭的和睦水火不容。我的天职是惧怕它,不信任它。”【24】这段话表现了拉拉在情感满足和宗教压抑之间、在灵与肉的结合中苦苦挣扎、矛盾的心境。她已把日瓦戈医生当作自己的爱情偶像和生活的保护神。日瓦戈除了眷恋她的美貌之外,更重要的是她追寻自由与幸福的勇气和坚定。他高度认同拉拉受伤的美:“我不爱没有过失、未曾失足或跌过跤的人,她们的美没有生气,价值不高。”“我爱你爱到顶点,永远永远爱你。”【25】他与拉拉的爱穿越了人间的世俗藩篱,是灵与肉的高度和谐,自由的充分体现、个性的充分张扬、人性的充分肯定,但他们毕竟是非法的情侣,双方都对家庭心怀愧疚。由于受到道德批判与宗教思想的藩篱,这段在动荡岁月中燃烧的爱情,最终还是在时势的风雨中湮没了。
拉拉与这三个男人的爱情悲剧,与他们受到俄罗斯宗教哲学思想的深刻影响密不可分,既有基督教中的禁欲主义思想,又有东正教中的“男尊女卑”思想。从上述分析可看出,拉拉与他们的爱情悲剧,无不体现着俄罗斯宗教思想的深深烙印。
三、 意象中的宗教因素
(一)光
这部小说中多次出现的意象就是“光”,日瓦戈与拉拉的几次相遇都与“光”的意象有关。第一次出现是在黑山饭店,在黑糊糊的外间里,因为眼睛没别的地方可看,日瓦戈就朝没有灯光的半间房里望着。“……餐桌的那边,一个姑娘坐在扶手椅上睡觉,……从屏风后面出来的却是另一个人。……他把从灯架上取下来的那盏灯举在头顶上,走到姑娘睡觉的那张书桌跟前,把它放在灯架上。亮光惊醒了那个姑娘。”尤拉“死死地盯着他们。他从谁也看不见的昏暗中不转眼地望着灯光照亮的地方。”【26】第二次出现是在日瓦戈与冬妮娅去斯文季茨基家参加圣诞晚会,驱车路过拉拉和安季波夫所在的房子时,日瓦戈偶然看见“一扇玻璃窗上的窗花被烛火融化出一个圆圈,似乎在等待着谁”,这时他默念:“桌上点着一枝蜡烛,点着一枝蜡烛……”【27】此外,日瓦戈与安季波夫都有同样的感触,就是拉拉到来便会带来“光明、温暖、希望、生命力”等。如日瓦格说“只要走到她(拉拉)身边用手指一碰,迸出的火花便会照亮房间……”【28】而斯特列尔尼科夫也曾在谈及拉拉时说“当她走进房间时,窗户仿佛都敞开了,里面充满了空气和阳光”【29】。当拉拉离去,当他们的爱情离去的时刻,也就是“光”的意象消隐、“黑暗”的意象重新出现的时刻。在此,“光”的意象不仅暗示着日瓦戈与拉拉冥冥中注定相遇,也暗示拉拉拥有促使事物更新、复苏的力量,同第一部分拉拉的圣母玛利亚宗教原型正好相符。而小说中日瓦戈寻找的代表新生和希望的精神力量正是拉拉身上所拥有的。
在《圣经·约翰福音》中耶稣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因此,小说中的“光”还是对于人生命永恒的祈祷和对一个人生命的神秘光辉的赞颂。它将尤拉和拉拉的爱情生命点燃,又随着尤拉的逝去在拉拉的心中继续燃烧,象征着日瓦戈的生命之火在拉拉身上的“复活”。
(二)日瓦戈的诗作、札记等
日瓦戈说过“在别人心中存在的人,就是这个人的灵魂。这才是您本身,才是您的意识在一生当中赖以呼吸、营养以及陶醉的东西。这也就是您的灵魂、您的不朽和存在于他人身上的您的生命……这意味着您曾经存在于他人身上,还要在他人生上存在下去。”【30】他把自己的诗作看作是灵魂永生的寄托,虽作为一名医生一事无成,但他却希望在自己的诗文中获得永恒价值。艺术是永恒的,艺术家也当属于永恒。成年日瓦戈真切的感觉到自己对普遍存在的永生的参与,并把他视为生命意义的全部的艺术作为神的启示的继续,存在于他的整个生命之中,存在于他死后复活的生命之中。如在小说结尾部分,戈尔东和杜多留夫坐在一起翻看日瓦戈所写的札记,“这些都是他们看过无数次的,一半几乎都能背下来。”“坐在窗前的这两位已经老了的朋友感觉到,心灵里的自由已经到来……已经可以触及到未来,他们两个也在步入未来,而且现在已经身在其中。”【31】日瓦戈的后代在苦难的俄罗斯大地上执著顽强地生活,表明日瓦戈虽已逝去,但他的灵魂、他的精神获得了“复活”、得到了“永生”,并且作为一种永恒价值存在于每个人的心中。这也与小说开头日瓦戈母亲葬礼中人们所唱的葬歌《永志不忘》达到了呼应。
四、 结语
通过上述从人物形象、情节、意象等三个方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在《日瓦戈医生》中体现的宗教因素是很浓厚的。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作者赋予小说人物一种宗教原型亦或传道者的身份,使他们身上具备宗教的神性思维,从而达到深化小说“死亡”“永生”主题的作用;在情节安排中,有关拉拉感情悲剧的描写深刻反映了俄罗斯知识分子受基督教禁欲主义与东正教“男尊女卑”思想的双重影响;在意象的描写上,作者更是力图表现小说“灵魂不死”“精神永生”的主题,以表达他对俄罗斯民族超越苦难生活、追求永恒真理的希望。
总之,作品中涉及宗教因素的例子很多,上述分析的三个方面只是其中一隅。作为一名俄罗斯作家,帕斯捷尔纳克身上具有深沉的俄罗斯宗教文化烙印。小说中之所以会有如此浓郁的宗教因素,与俄罗斯社会当时盛行东正教的社会环境及作者自身的犹太人身份及犹太教哈西德派的宗教信仰有很大关系。作者借宗教这一充满神圣性的思想载体,向人们传达了关于历史、社会、艺术、生命等一系列有关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思考,是一部真正的人类社会“启示录”,值得我们长期研究、学习。
参考文献:
【1】季明举:生命的神性书写———《日瓦戈医生》中的价值超越维度.[J].当代外国文学,2010
【2】任光宣:俄罗斯文学简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6年
【3】帕斯捷尔纳克:人与事.[M].乌兰汗等译.北京:三联书店,1991年.
【4】米·爱普施坦:哈西德派与塔木德派:帕斯捷尔纳克与曼德尔施塔姆创作比较研究.李志强译.俄罗斯文学讲座.四川大学外国语学院
【5】【6】【7】【8】【9】【10】【11】【12】【13】【14】【15】【16】【17】【18】【19】【20】【21】【22】【23】【24】【25】【26】【27】【28】【29】【30】【31】(苏联)鲍·帕斯捷尔纳克著:日瓦戈医生.[M]张秉衡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
 最新评论
最新评论|
版权所有© 中外文学研究课题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