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版权所有© 中外文学研究课题组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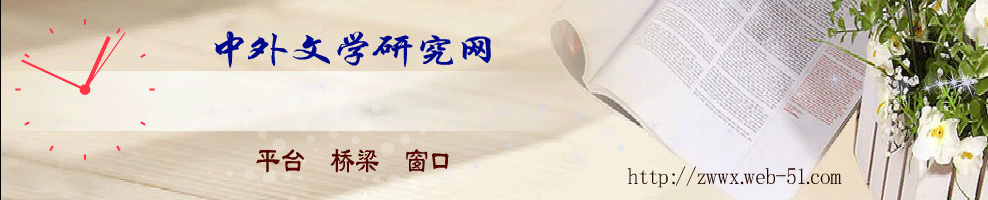
学校:西北师范大学 专业: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 姓名:曹慧敏
【摘要】艾柯作为一位百科全书式的作家,他的作品有着浓厚的宗教氛围。《玫瑰的名字》以侦探小说的方式反映了艾柯对于现实的思考。宗教因素在其创作中占有重要的位置。本文将从小说结构、小说主题、小说内容方面看在宗教背景下艾柯的创作。
【关键字】安伯托·艾柯 宗教 “道” 笑
中华文化以佛教最盛,在西北的甘南藏族自治区,藏传佛教在这片辽阔的草原上得到了长足的发展,而拉卜楞寺,作为古代安多地区藏族文化之大成,不仅是文学艺术的宝库,而且也是一个历史资料、文物的博物馆。在中世纪的意大利,同样拥有这样的一个修道院,它是当时世界的一个缩影,拥有世界上最大的图书馆。只是昔日的巴比伦王朝的荣耀已然消逝,这座修道院也在一场大火中付之一炬。隐藏在背后的却是一场令人惊惧的凶杀案。80岁的阿德索修士让我们见证了18岁的他所经历的那场灾难,如今这一切都已消逝,成为没有涯际漫游不止的符号尘埃,留下的是我们对于现世的思考。
一、安伯托·艾柯
安伯托·艾柯(1932——)(Umberto Eco),当代意大利哲学家、符号学家、文艺理论家、作家。他思想睿智,知识渊博,在哲学、美学、宗教、历史、文学批评和文化批评等领域有独特的贡献。他是一个百科全书式的作家,轻松地游走于经院主义、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理性与非理性、实用主义与结构主义之间;既横跨诸多领域取得了经典性建树,又置身时事前沿发出知识分子独立的呐喊。《剑桥意大利文学史》将艾柯与意大利诗人普里莫·莱维和作家伊塔洛·卡尔维诺齐名,将其誉为“20世纪后半期最耀眼的意大利作家”。正如意大利学者卡尔维诺所指出的那样,“二十世纪伟大小说表现的思想是开放型的百科全书”[1]。艾柯目前问世的小说几乎每一部都是百科全书式的范本,令读者惊喜不断。同时出版于1956年的《托马斯·阿奎那的美学问题》奠定了他作为“中世纪学者”的地位。中世纪对于他而言是一个驰骋想象的空间,对他而言是一种持久的诱惑:在任何地方都能看到中世纪。他的小说也正是他研究中世纪的体现。
1980年出版的《玫瑰的名字》是艾柯的第一部小说,讲述了14世纪背景下,博学多才的威廉修士和见习修士阿德索奉奥匈帝国皇帝之命前往意大利北部山区的一个修道院去调查其中可能存在的异端之举。在初到修道院时受院长所托调查发生在修道院的一系列谋杀案件,七天内有七位修士皆以怪异恐怖的方式死于非命。威廉根据事件的表象通过推理判定凶手可能参照《圣经·启示录》实施谋杀并在追查凶手的下落时发现一切皆因亚里士多德《诗学》下卷所致,凶手豪尔赫将其视为禁书加以保护,并且在书页上涂了剧毒。在威廉因为偶然揭开事件真相时,豪尔赫将书吞食并且随着大火与修道院化为灰烬。
这部小说与他的其他几部小说一样是艾柯符号学、诠释学理论的延伸。“在某种意义上,他的四部长篇小说皆可视为其高深理论的通俗版百科全书,它们本身就是关于符号系统的符号系统,关于阐释学的阐释学,是艾柯借以表现自己学说理论的文学载体。”[2]但除却近年来以艾柯的符号学、诠释学理论作为基点对《玫瑰的名字 》进行的研究之外,这部小说中的宗教因素同样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无论从小说结构、小说主题、小说内容来看,都有着借中世纪背景来对反映作家对现实的思考。
二、宗教框架下的小说
1. 外部框架
首先从小说的题目来看,《玫瑰的名字》,在小说中与其并没有多大的关联,直至小说最后一句引用了12世纪修士莫尔莱的贝克纳的诗句“昔日玫瑰以其名流芳,今人所持唯玫瑰之名。”[3]才出现题目。而艾柯所留给我们的思考却是深远的。较之于具体事物,在时间的流逝中,唯有符号可以被我们所掌握。正是由于玫瑰意象的多重性,在当时的学界曾引起关于玫瑰之名的“大战”。而艾柯正是希望通过这个意象的丰富性与多义性来提倡阐释,引发读者无尽的诠释。
其次小说以见习修士阿德索的眼光描述了七日之内发生在修道院的谋杀案,同时又按照做礼拜的时辰将每天分为申正经、赞美经、晨祷、辰时经、午时经、午后经、夕祷和晚祷。在看似有序的叙述中,又插入了一系列对于园艺学、草药学、工艺学等的介绍。符号的无限衍义又加之凶案的发生,使一切又都陷入到无序之中。这种叙述方式,恰恰是艾柯想借小说来反映对于当今社会无序性的思考。“在他看来,世界的混沌性质是中世纪与后现代的相交点,也是世界的本质特点,他呼唤一种开放、联系且综合的思维方式,以应对这个非理性的世界”。[2]
2、内部结构
小说开头写到“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出自《圣经•约翰福音》的这句话,是整个中世纪神学的焦点,也暗含了小说的深层主题——逻各斯问题。
“道”是希腊文“逻各斯(logos)”的意译,原意为“言辞”,在哲学上的意思是“言说”或“理性”。 而逻各斯最精妙也最悖论的地方在于:它既是终极意义本身,又是追寻终极意义的方法。对于“道”,也即逻各斯的争论,贯穿于小说的始终,不仅体现在人物的设置上,采用了代表不同立场的修士,有以乌贝尔蒂诺、雷米乔为代表的圣方济各修会逻各斯救赎论的“信仰至上”观点,也有以贝尔纳德为代表的罗马教会逻各斯理性论的“理性至上”的论调;有阿维尼翁代表团的“教皇神学论”,也有皇帝代表团的“帝国神学论”。同是从基督教经典中寻求证据,观念上却那么针锋相对,相互的敌视和迫害更是令人发指,是对中世纪话语权之争的生动图解。 [4]而且对于具有与自己观点不同的教派,都将其视为“异端”,也就引起了“异端”与“正统”之间的论争,这条线成为小说的一条主要线索。
在某种意义上,西方文化一直是逻各斯文化,即一个需要终极意义和认识论的文化。走出中世纪哲学的神学逻辑阶段之后,现代哲学主流用“理性”置换了上帝,而后又用“语言”替代理性。
代表理性的威廉威廉是一个圣方济各修士,但同时他博是学多才,拥有各个领域丰富的知识,他“不仅知道如何读懂大自然这部巨著,还知道修士们如何读《圣经》的经书,又如何依据经书进行思考”[3]。他凭借着理性对事件进行分析,不断地接近真相,在破解接连不断的谋杀案时,威廉采用了《圣经•启示录》预言了末日审判时、七个天使吹号而出现异象:“第一位天使吹号,就有雹子与火搀着血丢在地上……第二位天使吹号,……海的三分之一变成血…… 第三位天使吹号,……水变苦……第四位天使吹号,日头的三分之一,月亮的三分之一,星辰的三分之一都被击打…… 第五位天使吹号……蝎子蛰人的痛苦……第六位天使吹号……约翰吃小书卷……” [3]就像所预示的那样,接连发生的命案迎合了这样的推论,把威廉一步步引入了对线索的执迷中,但事实上一切都是偶然,“阿德尔摩死在冰雹中,却是一起自杀;韦南齐奥死在血泊中,却是由于贝伦加古怪的念头;贝伦加死在水中,却是纯属偶然;塞维利诺死在浑天仪所示的第三部分,可那是因为浑天仪是马拉西亚当时唯一可以顺手取来击毙他的凶器。”[3]对于威廉而言,他一直坚信理性的力量,从自然那里获取知识,在最后,循着线索,他没有找到真相,反倒是因为阿德索的梦得到了破解的钥匙。偶然取代的必然,一切都是“偶然的巧合”威廉“按一个心灵邪恶却具有推理能力的人所设计的方案追寻到豪尔赫,事实上却没有任何方案,或者说豪尔赫是被自己当初的方案所击败,于是产生了一连串相互矛盾和制约的因果效应,事情按照各自的规律进展,并不产生方案。”[3]对于逻各斯的狂热最终将事件推向一发不可收拾的境地。威廉力图去追寻着表面的秩序,但事实上“宇宙本无秩序”。不断接近真相的过程是不断地在编写谎言,而豪尔赫出于对信仰的狂热追求不惜成为“杀人凶手” ,对于信仰的狂热追求,同样使他走向了毁灭。逻各斯所力图给人们提供的是一个终极目的,而世界本无秩序就是对终极目标的驳斥。艾柯对于逻各斯中心主义的批判也可以从这里得到确认。
小说是处于人老发白,苦度残年的阿德索对于18岁时自己的经历的叙述,期间除却见证修道院的毁灭,对于阿德索而言,他的内心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不久,我将重新开始我的生命,我不再相信那是上帝的荣耀,虽然我所属教会的修道院院长们总是那样谆谆教导我;也不再相信那是上帝的欢乐,虽然当时的方济各修士们都那样相信,甚而不再相信那是虔诚。上帝是唱高调的虚无,‘现在’和‘这里’都触碰不到它。”[3]信仰宗教的阿德索最终将一切归于“虚无”,正是反映了在那个宗教混乱的时代,人失去皈依后对于自身的思考。
三、 小说内容
(一)笑的讨论
豪尔赫笃信宗教,将揭示真理的亚里士多德的《诗学》下卷视为是亵渎上帝威名的书,对于他而言“那是‘哲人’的书。亚里士多德的每一部书,都颠覆了基督教几个世纪以来所积累的部分智慧。神父们谆谆教诲的是圣言力量之所在的道理,而只要波伊提乌评论到哲人的话,圣言之超人的神秘,就变成人类范畴和演绎推理的拙劣模仿了。”而对于他而言,“笑”是人类“血肉之躯的弱点,是堕落和愚钝之举。是乡下人的消遣,是醉汉的放纵。……笑毕竟是卑微的,是贱民护身的法宝,平民还俗的奥秘。”[3]小说的隐性线索就是豪尔赫与威廉关于“笑”的争论。
在图书装饰员阿德尔摩的遗物中,威廉发现了想象力丰富的图画,这些怪诞的形象引起了修士们的赞叹,发出阵阵的笑声。但豪尔赫却很严肃地制止了大家,而威廉却认为“页边的图案常常引人发笑,但有教诲人的作用。”修士韦南齐奥赞同说,上帝透过扭曲的事物而存在,笑也是传播真理的工具。但豪尔赫则认为《圣经》上说“基督从来不放声大笑”韦南齐奥死后,威廉借机再次提起了关于“笑”的话题,他认为“‘笑‘是一种良药,就像沐浴一样,能够陶冶人的性情,调节人的情感,尤其是治疗忧郁症。”而豪尔赫则认为“笑的人既不相信也不憎恶他所笑的对象。对罪恶报之以笑,说明他不想与之抗争;对善行报之以笑,说明他不承认善德自行发扬光大的力量。”,对于《诗学》第二卷的内容,我们不知道,但艾柯在文中却描述道“喜剧产生乡下人居住的农村,当初是作为盛宴或聚会之后欢乐的庆祝活动。剧中讲述的不是有名望或者有权势的人,而是卑微和可笑的人,不是刁蛮的人,故事也不是以人物的死亡为结局。喜剧往往用表现贱民的缺点和陋习来达到滑稽可笑的效果。”[3]对于豪尔赫而言,亚里士多德对于喜剧的定义是对传统的否定,随之而来的是对大众文化的极力鼓动。“如果‘笑’是平民的乐趣,平民的纵欲则应该用‘严肃’来控制和打击,而且应该受到‘严肃’的威慑。而平民没有手段来完善‘笑’,以使它变成对抗牧师的‘严肃’的工具。……然而如果有一天,某人引用哲人的言论,俨然以哲人的口吻说话,把‘笑’的艺术提升为一种微妙的武器,如果戏谑取代了信仰,如果至高无上的最神圣形象被颠覆了,取代了悉心拯救人类的救赎形象,啊,到了那天,威廉,就连你和你的学识也会被颠覆的。”[3]豪尔赫所担心的是来自知识分子内部对这种笑和颠覆的认同。亚里士多德是一种象征,代表着几百年来为追求真理和理性不断否定传承,否定自我的知识阶层。现代社会的快节奏所造就的是精神的匮乏,现代人在恶搞的笑声中消弭了敬畏之心。豪尔赫深知这个所以也力图消灭它。豪尔赫对于《诗学》第二卷的评价,正是“它使颠倒了的东西成为合理,……使‘笑’……竟成为哲学和伪神学的研究对象。”文学会“像帕尼罗帕一样,在夜里拆坏神学家和哲学家……前一天编好的地毯”。它既可以成为对“上帝之笑”的回应、“笑天下可笑之人”;又可能以“笑”颠覆价值、颠覆传统,代之以“审美的统治”。艾柯正是通过这些再现了“理性和智力”的不断受骗,“真理与虚构、现实与欺骗之间的游移”,亦即主人公所经历的“一次令人瞩目的转变;从现代的确定性……到后现代的不确定性。”[5]
(二)基督是否贫穷
小说中,整个修道院就像是一个世界的缩影,其中关于圣方济各和罗马教廷关于基督是否贫穷是宗教裁判所和宗教异端产生的最主要的因素。对于阿德索而言,他“为差异的本身而困惑。”他向威廉寻找答案,“跟乌贝尔蒂诺谈话的过程中,您极力对他表明异教徒和圣人都是一样的,可您跟修道院院长谈话时却又竭力跟他解释异教徒与异教徒以及异教与正统的基督教的差别。也就是说,您责备乌贝尔蒂诺把本质相同的异教徒区别对待,却责备修道院院长把本质不同的人看作一丘之貉。”[3]阿德索对于宗教派别之间的差异充满了疑惑,包括他对萨尔瓦多雷所说的部分认同,反映了12世纪以来宗教的混乱以及人们信仰的危机。但作为他导师的威廉同样无法区分,辞去宗教裁判所的职位,不仅仅只是出于道德,也是因为他看不出其中的差异。 这样就导致了威廉人物形象上的多重性,甚或复杂性。这并不是作者的事,而是源于知识阶层自身的某些特点和历史传统。
四、结语
综上所述,艾柯对于中世纪的书写,并不停留在对历史的反思,更多的是对于现实的思考。于他而言,将对于社会的责任和负载的历史使命投诸于诗性文字。“只有通过诗的语言才能完全表达,因为诗综合了对世界的想象和现实,唯有通过诗,人们才能看清其历史地位。”[6]有良知的“文化人”首先付诸行动的就是通过诗性符号,弥合理性与信仰的距离,缝合历史与现实的绽裂。艾柯的作品为我们提供了一种解读现代的方式,留给了我们更多的阐释空间,值得我们去关注和了解。
参考文献:
[1]孙慧·艾柯文艺思想研究[M].山东:山东大学出版社,2015
[2]马凌·后现代主义中的学院派小说家[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4.7
[3]埃科·玫瑰的名字[M].沈萼梅 刘锡荣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0.3
[4]马凌·诠释、过度诠释与逻各斯[J].外国文学评论,2003.1
[5]杨慧林·“笑”的颠覆性与神学逻辑[J].问题.2003.2
[6]安伯托·艾柯·误读[M].吴燕莛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5.3
 最新评论
最新评论|
版权所有© 中外文学研究课题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