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版权所有© 中外文学研究课题组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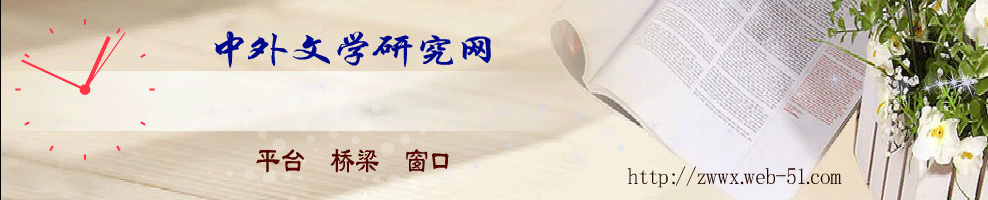
李晓卫
(西北师范大学 文学院,甘肃 兰州 730070)
[提 要]“十七年文学”的代表作家柳青坚持用典型理论来塑造人物形象,而作为新时期现实主义文学的领军人物,陈忠实在遵循典型理论的前提下注重吸收和运用文化心理结构的理论和方法,通过对人物的文化心理结构的剖析,塑造出了生活内涵丰富、文化底蕴深厚的人物形象,从而实现了对柳青典型理论和创作的升华、超越及其对现实主义的发展与深化。
[关 键 词] 典型理论 文化心理结构 现实主义 发展 深化
作为新时期现实主义文学的代表作家,陈忠实的创作在现实主义的观念和方法上较之以前的现实主义有了较大的发展和深化。他在谈到自己创作中现实主义所注重的人物形象塑造的体会时说:“我过去遵从塑造性格说,我后来很信服心理结构说;我以为解析透一个人物的文化心理结构而且抓住不放,便会较为准确真实的抓住一个人物的生命轨迹;这与性格说不仅不对立也不矛盾,反而比性格说更深刻了一层,这就是我所理解的心理真实。”①不难看出,陈忠实创作之初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与作为他的老师之一的柳青持相同的理论和方法。但是,通过长期艰苦的艺术探索和实践磨练,陈忠实在以后的创作过程中,寻找和把握住了更为深刻也更为成功的人物形象塑造理论和方法,塑造出了更为出色的艺术形象,从而实现了对柳青的超越和对现实主义的发展与深化。
一
柳青作为“十七年文学”代表作家之一,在创作上信奉和遵从马克思主义的典型理论,特别推崇恩格斯关于“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的学说。他说:“艺术上的典型学说,从亚理斯多德经过黑格尔到恩格斯,进入一个新的阶段,这就是典型环境的典型性格学说。”关于典型性格柳青解释道:“人物的社会意识的阶级特征、社会生活的职业特征和个性特征,互相渗透和互相交融,形成了某个人的性格,就是典型性格。三种特征不是混合起来,而是活生生地结合起来,成为一个活的人,就是典型。没有阶级特征不能成为典型,没有职业特征也不能成为典型,没有个性特征也不能成为典型。三种特征高度结合,就具有充分的典型性。”“前二者就是人们所说的共性,后者就是人们所说的个性。文学作品如果只写了一个人的个性特征,而缺乏共性特征,甚至没有共性特征,不能任意把它说成典型。”②关于典型环境柳青这样解释:“按照一定历史时期的广阔历史背景创造的环境就是作品的典型环境,这个环境既有普遍性,又具有特殊性了。片面地强调了特殊性,就失掉了规律性。”柳青又根据他对这个问题的理解,认为“有理由把典型环境解释为典型冲突”。他还进一步阐述了对典型性格与典型环境关系的理解:“我们马克思主义者所要求的典型性格,必须在典型的冲突中表现出来,而不可能在一些非典型的冲突中或静止的状态中表示出来。”③
从这些阐述来看,柳青对马克思主义典型理论的认识和理解是基本准确的。但是,由于时代和作者的思想局限,当他把典型理论运用到创作上就出现了明显的偏差和失误,这在梁生宝形象的塑造上表现得尤为突出,柳青认为典型性格应该在典型环境和典型冲突中加以表现和塑造,这是不错的。但是,他对典型环境和典型冲突的理解却有着明显的失误,他把典型环境和典型冲突狭隘地解释为阶级斗争,认为,“离开了阶级斗争的典型冲突和两条道路的典型冲突,人们连一个典型性格也创造不出来,……”④所以当他把这一理论运用到创作上就出现了明显的偏差,具体来说就是对当时的典型环境和典型冲突的理解和表现不准确。柳青在长篇小说《创业史》中,把20世纪50年代的中国农村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环境看成是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典型冲突,这样,就排除了其他多种社会的和文化的因素,而把丰富的社会生活内容纳入了阶级斗争的单一模式之中,使人物形象置身于一个虚假的“典型环境”里,在这样的“典型环境”里“塑造”出来的“典型性格”就不可能对生活本质做出真实的反映,也就不能真正称得上是“典型性格”。根据20世纪50年代中国农村的实际情况,一个现实主义作家应该塑造出既向往新生活,又因袭着各种旧的思想文化传统,在放弃私有制,接受公有制的道路上艰难行进的复杂矛盾的形象,这样才能概括出那一时期农村生活的基本动向。遗憾的是,我们在《创业史》里基本看不到这样的形象。有些评论者认为,“《创业史》中梁生宝同郭振山之间的矛盾冲突,是柳青对于社会主义革命初期农村现实生活中矛盾冲突的新的思考和新的发现。”⑤而实际上是对现实生活中一般矛盾的拔高。读过柳青散文作品的读者应该不会陌生,在《灯塔,照耀着我们吧!》一文中,作为梁生宝和郭振山生活原型的王家斌和高梦生之间并没有《创业史》中那么尖锐的矛盾冲突,然而,到《创业史》里,梁生宝与郭振山的矛盾却被写成重要的矛盾。而且按照柳青的说法,这个冲突在以后几部里还要逐渐加深。实际情况也确实如此,在第二部里,矛盾冲突就主要由阶级斗争转向路线斗争,合作社与姚士杰、郭世富等的矛盾已退居次要地位。尽管有评论者惋惜小说未能写完,无法使人通览斗争的全貌。但笔者认为这对柳青来说应该是幸事,否则,我们看到的也许会是象《艳阳天》那样一部肆意渲染阶级斗争的作品。
二
对于陈忠实来说,虽然他的早期创作深受柳青的影响,他最初的文学观念的形成也离不开当时那种特定的时代氛围而留下一定的痕迹,但是,通过长期的创作实践和艰苦的艺术磨练,陈忠实的文学观和创作观已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与柳青及其那个时代的文学观和创作观都有着明显的不同。陈忠实在谈到他的文学观和创作观时多次坦诚地表达过相似的见解,比如,他说“文学仅仅只是一种个人兴趣。” “创作实际上也不过是一种体验的展示。”⑥ “单就个人的因素看,写作确实就是一种兴趣和爱好。” “虽然也是在任何冠冕堂皇的场合都要讲是为革命写作,其实是以文学创作为寻找自己的人生出路,尽管如此,选择文学的动力还是对文学的兴趣。” ⑦从陈忠实的表白不难看出,他的文学观与柳青以及与他自己以前的文学观相比,都发生了较大的变化。这种变化消解了罩在文学上的神圣的光环,使它脱离了本不应当承担的过多的使命而回归到了自己应有位置。对于陈忠实来说,文学观念的变化必然引起创作的变化,从而使他能够以一种平常心来对待文学和从事创作。随着对文学创作的新的认识和理解的产生,陈忠实的创作在80年代中期发生了重大转折。对此他解释说:“八十年代中期,文学创作和理论都非常活跃,所有新鲜理论不论是中国的还是外国的对我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尤其是关于创作的人物心理结构学说、文化心理结构学说。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到接触到这个理论以前,接受并尊崇的是塑造人物典型理论,它一直是我所遵循和实践着的理论,我也很尊重这个理论。你怎么能写活人物、写透人物、塑造出典型来?文化心理结构学说给我一个重要的启示,就是要进入到你要塑造的人物的心理结构并解析,而解析的钥匙是文化。这以后,我比较自觉地思考中国人的文化心理,从几千年的民族历史上对这个民族产生最重要的影响的儒家文化,看当代中国人心理结构的内在形态和外在特征,以某种新奇而又神秘的感觉从这个角度探视我所要塑造和表现的人物。” ⑧
应该说陈忠实经过长期的艺术实践和探索,终于找到了一种塑造人物形象、刻画人物性格的十分有效的新的理论和方法。正如他所说的那样,文化心理结构这种新的理论和方法与塑造人物形象的典型理论及其性格学说并不对立和矛盾,而是比性格学说更为深刻。陈忠实的创作之所以能够超越柳青而在中国当代文坛上占有独特的地位,除了其他方面的因素之外,在人物形象塑造上的这种观念和方法的创新无疑也是其中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陈忠实在创作中紧紧抓住了几千年来对中国社会和人物心理具有绝对制约和支配作用的儒家文化来塑造人物形象、刻画人物性格,这样,就使他笔下的人物形象具有了更为丰富的文化内涵,包含着更为深广的社会历史内容。
三
客观地说陈忠实早期短篇小说创作中主题思想的开掘还不够深厚,作者对所表现内容的思考也不够深入,基本上还是停留在对现实生活、政治观念的直接、简单的描写和反映上,因而,人物形象的塑造也是比较平面化的。从《早晨》、《第一刀》、《初夏时节》等短篇小说的人物形象塑造来看,对年轻一代的描写还显得比较单薄,比如,《初夏时节》中的冯豹子形象还缺乏思想的深度和艺术的高度,在他身上似乎还存在着《创业史》中的梁生宝的痕迹。在《徐家园三老汉》中,对思想境界比较高的徐长林老汉的描写还有一些概念化的痕迹,在他的有关言谈中,政治意味还较浓厚,对其先进思想的表述也稍嫌直白。当然,作为一个不懈地追求创作的独特性的作家,陈忠实的创作不会永远停留在一个水平线上而是在不断地探索和前进的。在他的创作的发展中,逐渐表现出了与其他作家不同的思想艺术追求,体现出了他在人物形象塑造上的那种注重人物心理文化结构的独特的理论和方法,而陈忠实的这种认识及其运用也经历了一个逐渐成熟的过程。
在80年代初创作的短篇小说《尤代表轶事》中,已初步显露了陈忠实那种独特追求的端倪。小说塑造了尤喜明这个性格被严重扭曲的独特的农民形象,从而反映了建国以来党在政策上的一些失误所带来的危害。然而,更值得人们关注的是,作者把笔触深入到人物的内心深处,从更加广阔的历史背景上解析其独特的文化心理结构,挖掘造成人物畸形性格的深层原因。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陈忠实继承了鲁迅的现实主义传统,从文化根源上挖掘民族劣根性的原因,“画出国民的灵魂”。
80 年代中期以后,在《梆子老太》、《蓝袍先生》等中篇小说中,更加注重通过对人物的文化心理结构的解析来塑造形象、刻画性格,其中《梆子老太》就比较明显地体现陈忠实在创作上的这种艺术追求。
小说塑造了一个悲剧性人物形象黄桂英,绰号“梆子老太”。这也是一个性格被严重扭曲的形象。黄桂英与千千万万普通的中国劳动妇女一样,按照传统的方式被一顶轿子抬进梆子井村,嫁给了弹棉花的手艺人胡景荣,虽然她的针线活和茶饭不能令人满意,但干起农活来却是一把好手,丝毫不比男人逊色。因此,起初胡景荣母子对娶来的新媳妇并不十分满意,但也还基本能够接受。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问题出现了,黄桂英不能生育。对于在儒家传统文化的氛围中生活的农民们来说,这是一个无论如何也不能接受的事实,不仅胡景荣母子不能接受,就是黄桂英自己也无法接受。传统观念和人们的议论,给黄桂英的心理上造成了巨大的压力。在长期的精神压抑下,她的心灵被扭曲,由不能生育的自卑发展到希望别人也与她一样的“盼人穷”。她在村子里拉扯闲话、搬弄是非,希望能够找到自己的“同类”,以分担和缓解她的压力。但是,愿望却一次次地落空,她的心理负担越来越重了,在人面前抬不起头来。然而,谁都没有料到后来发生的政治运动却把黄桂英推到了梆子井村的显赫位置,成就了她一生中的一段辉煌。在“四清运动”中,黄桂英的多嘴多舌被工作组所利用,把她作为阶级觉悟高的典型来宣传,在运动结束时被工作组任命为贫下中农协会主任。从此,黄桂英就被不知不觉地绑在了极左政治的战车上,开始了自己连做梦都没有想到的政治生涯。“文革”时期,她自觉不自觉地充当了极左政治的工具,时时处处狠抓阶级斗争,打小报告,诬陷别人,对村民们构成了极大的威胁,她从“盼人穷”变成了“讨人嫌”,人们从烦她而变得怕她。而“梆子老太”的那种变态的政治积极性,也深受上级部门的赏识,让她到处去参加活学活用的讲用会、“积代会”,向别人介绍她的“经验”。时间一长,“梆子老太”也逐渐习惯和适应了这种生活,只要几天不去开会她就心里憋得发慌,虽然她在外面很有名气,但是,在梆子井村乃至自己的家里都彻底地孤立了。正当“梆子老太”已经习惯了她的那种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的时候,改革开放的春天来到了,社会生活和人们的思想观念都发生了巨大变化,而对这种变化,“梆子老太”却无法理解和适应了。当党和国家开始纠正过去的错误路线造成的后果,梆子井村也给以前的那些冤假错案平凡时,“梆子老太”首先就无法接受,她本能地想着难道过去的阶级斗争都抓错了?后来,当党和国家进一步调整深化农村改革,制定出一些新的政策时,“梆子老太”更是无法理解了。比如,当公社书记在会议上传达党的在农村各级政权中取消贫下中农协会的机构、以后再没有贫下中农这个提法、只说社员的精神时,“梆子老太”怀疑自己的耳朵是否出了毛病,她确实有一肚子想不通的问题。“贫协会”取消后梆子老太的精神彻底崩溃了,她百思不得其解,怪她什么呢?她错在哪里呢?她当贫协主任,难道不是众人举拳头选举的吗?她当临时领导小组组长,难道不是那两位解放军的命令吗?让她抓对阶级敌人的斗争,难道不是各级领导每一次会议布置的要求吗?她从公社到地区去“讲用”,难道是她自己能决定的事吗?现在,梆子井村的庄稼人,不管这些事情是谁布置她做的,只是鄙夷地朝她翻白眼。在自我反思中“梆子老太”始终没有也无法找到造成这种结局的原因,最后,只能戴着沉重的精神枷锁在痛苦和压抑中死去。
陈忠实对“梆子老太”这个人物形象塑造的独特之处以及这篇小说在他的创作中所达到的新的高度,就在于他运用文化心理结构的理论,紧紧抓住影响人物性格的深层原因来描写和塑造人物,而没有仅仅停留在典型理论关于人物性格的共性和个性的勾勒上,更没有象柳青那样局限于阶级斗争的观念来刻画人物性格。运用文化心理结构来解析人物性格,实际上就是更加强调和重视人物行为的社会文化背景,挖掘造成人物行为的更深层次的原因。这就使得他笔下的这个人物形象具有了相当的思想深度,从中可以窥见传统文化对国人的那种根深蒂固的影响。
从“梆子老太”形象来看,她的那种从“盼人穷”到“讨人嫌”的畸形性格的形成固然有着鲜明的现实政治的背景,正是当时那种极左的政治路线造就了她的畸形性格,所以,说她是极左政治的产物并不过分。但是,如果对造成人物畸形性格的原因的分析仅仅停留在这一步,那就还没有找到更为深刻的原因,那样一来,“梆子老太”的畸形性格带给人们的警示作用也就不会太大。而陈忠实的高超之处就正在于他紧紧抓住了文化心理结构这把钥匙,剖析造成人物畸形性格的深层原因,从而促使人们对这个人物的悲剧性命运以及对造成她畸形性格的原因深入思考。从根子上来看,正是几千年来的儒家传统文化中的某些思想观念造成了“梆子老太”的畸形性格,比如“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等封建伦理道德。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女人在家庭中的作用主要就是作为传宗接代的生殖工具,除此之外就是操持家务、相夫教子。但是,“梆子老太”完全不符合这样的伦理标准。首先她不能生育,这在传统伦理道德的文化环境中就等于给梆子老太宣判了死刑,她是一个没有用的女人。不仅如此,“梆子老太”不善女工和茶饭,不会操持家务,对一个生活在儒家传统文化氛围中的女人来说,这也是一个很大的缺憾。由于“梆子老太”所具有的这些“天生”的缺陷,使她不被传统文化所接纳,这就给她心理上造成了巨大压力,促使她的性格扭曲和变形。在极度的精神压抑下,她最初也只能是希望有人与她一样,以减轻自己的精神负担。而一旦外界条件成熟后,她的那种被极度压抑的心理又会极度膨胀,从而导致了她在“文革”时期的那一段“辉煌”经历。可以说,她在一个错误的时期充当了一个错误的角色,这就使她的本来已经变形的性格又被极度的扭曲,最终成为一个死了都无人埋的讨人嫌的“瘟神”。“梆子老太”的可悲之处在于她至死不明白自己错在什么地方,以她的水平也无法弄明白。人生最大的悲哀就是不知自己的可悲。“梆子老太”的一生是可悲的,而造成她可悲命运的原因更值得人们去深思。陈忠实通过对这个人物形象的塑造深入审视传统文化,拷问国民的灵魂,这也许就是作者运用文化心理结构剖析和塑造人物性格的意义之所在吧。
经过长期的生活体验、生命体验和艺术实践,陈忠实积累了丰富的创作经验,对文学创作及其意义和作用也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和体会。因此,在长篇小说《白鹿原》的创作中他就能够更加自觉地运用一些新的创作理论来描写生活、塑造形象,表达他对生活的独特感受和艺术追求。既遵循现实主义的典型形象塑造理论,同时,又运用文化心理结构等创作理论从更深的层面上把握特定时代的社会环境和社会心理的真实、把握人物心理的真实。怎样写活人物、塑造典型?陈忠实认为文化心理结构学说给他一个重要的启示, “……《白鹿原》也是在这样的创作思路下开始构想的。它展现的不仅是两个个别的、具体的、家庭的文化心理结构,而且是整个民族的精神和心理结构。” ⑨
在《白鹿原》色彩斑斓的人物形象画廊中,作者在不少形象的塑造上都有意识地运用文化心理结构理论去解析人物心理、刻画人物性格,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就是白嘉轩。陈忠实在塑造这个人物时注重把他放在中国传统农业社会和儒家文化的环境和氛围中来加以考察和描写,以儒家文化的道德标准为尺度来解析他的文化心理结构,从而表现特定时代的社会心理真实和人物心理真实,塑造出了一个具有深厚历史内涵和文化底蕴的独特形象,在白嘉轩身上充分反映了作者对中国农业文明的认知和对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传统文化的态度。如果说白嘉轩的姐夫
总之,白嘉轩形象是作者运用文化心理结构的方法塑造出来的一个充分体现了历史真实、具有深广的社会内容和独特审美价值的艺术形象,从而使之毫无愧色地居于中国当代文学优秀人物形象画廊之列。
陈忠实在《白鹿原》中对黑娃这一独特农民形象的塑造,也是注重通过对人物文化心理结构的解析来进行的。作品集中描写了黑娃那种自幼形成的倔强性格和桀骜不驯的精神气质与传统文化的矛盾与冲突,并最终皈依传统的过程。作为一个普通的农民,黑娃倔强的性格在他幼小的心灵中播下了反抗的种子,萌发了叛逆的精神。早在孩提时代当族长白嘉轩资助他去念书时,黑娃却不耐烦地说:“干脆还是叫我去割草。”当鹿兆鹏出于好意给他冰糖和点心时,不仅没有使他产生丝毫的感激之情,反而激起他的自卑和抵触心理。虽然只是一个农民,但黑娃不愿走父辈的老路,希望按照自己的设想去生活。所以他离家外出当长工,尽管还是过着受剥削的日子,但对他来说这毕竟是按照自己的意志做出的选择。这些描写使黑娃性格气质中独立不羁的特点得到充分展示,为他以后的一系列行动奠定了基础。正因如此,当鹿兆鹏在白鹿原上掀起“风搅雪”的革命风暴时,黑娃成为第一个积极参加者也就不难理解了。随着革命的发展,黑娃也逐渐地显示了他的独特生存价值。先是在鹿兆鹏的启发下放火烧了军阀的粮库,紧接着又成为白鹿原上农协会的骨干,以极大的热情参与了革命活动。然而,政治风云的变幻使黑娃的革命热情遭到了沉重打击。但他既没有像他的一些兄弟那样屈膝投降,也没有像另外一些兄弟那样血洒白鹿原,而是走上了一条独特而漫长的道路。经鹿兆鹏的引荐他加入了革命军队,并因才能出众而颇受上级器重。但是好景不长,由于势力的悬殊,他所在的部队在一次战斗中全军覆没。至此,黑娃那由自发的反抗意识发展而成的革命信念又一次遭到沉重打击。黑娃毕竟是一个在传统文化的氛围中长大的农家子弟,如果说此前他主要是以一种积极、主动的态度来反抗压迫的话,那么在以后则主要是以一种消极、被动的态度来反抗的。传统文化的负面影响开始在他的头脑中产生作用。一个偶然的机会黑娃落入土匪手中,面对生存的困境,走投无路的他思前想后,以痛哭一场的方式告别了过去而落草为寇。此时的黑娃对政治已心灰意冷,只求能苟全性命。所以,当后来鹿兆鹏和白孝文各自代表游击队和保安团多次前来游说、劝降时他都不为所动,企图在国、共之间寻找一条中间道路,黑娃的这种选择是其自身性格发展与传统文化冲突、妥协的必然归宿。尽管具有强烈的反抗和叛逆精神,但作为一个普通农民他对革命的认识和理解其实与土匪们的劫富济贫并无多大区别,明乎此也就找到了黑娃能够长期栖身于土匪之中的深层原因。然而,对黑娃的思想行为最具有影响的因素,应该说还是根深蒂固的传统文化。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传统文化具有较大的保守性,它提倡的是对现存制度的服从和维护而不是背叛和超越。因此,黑娃的落草也还不是他的最后归宿,在传统的感召下,他最终率众接受了招安,由一个现存制度的反抗者变成了维护者。至此,黑娃的反抗最终也没有能够跳出传统农民起义的模式,走着一条造反——招安的传统之路。而黑娃形象更深刻的蕴涵在于在传统文化的感召下,他在精神上向传统的彻底皈依。此后,他的确做了许多“好事”,如带头戒烟,整顿军纪等。在黑娃“悔过自新”的过程中,最重要的两件事是拜
至于小说中的其他人物
______________
注 释:
①陈忠实:《关于〈白鹿原〉与李星的答问》,见《陈忠实创作申诉》,花城出版社,1996年9月第1版,第27页。
②③④⑤柳 青:《典型·才能·气质》,见《人文杂志丛刊第1辑·柳青纪念文集》第274、278、279页。
⑥陈忠实:《兴趣与体验》,见《陈忠实创作申诉》,花城出版社,1996年9月第1版,第1、4页。
⑦⑧⑨陈忠实:《文学的信念与理想》,《文艺争鸣》2003年第1期。
本文发表于《甘肃社会科学》2007年第3期
 最新评论
最新评论|
版权所有© 中外文学研究课题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