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版权所有© 中外文学研究课题组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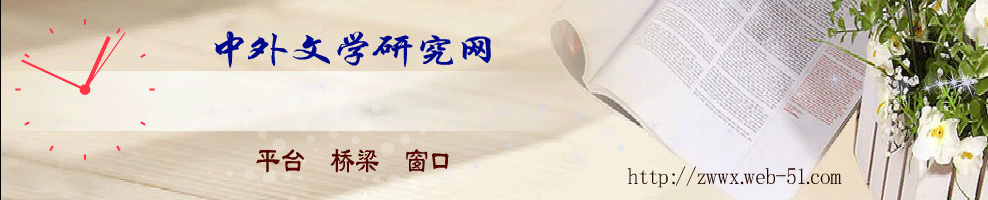
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 马粉英
摘要 叶塞宁是20世纪一二十年代俄罗斯杰出的诗人。评论界更多将他定位为“意象派”诗人,“新农民诗人”,细读叶塞宁诗歌,笔者认为叶塞宁也是一位生态诗人。他的诗歌世界中人与自然打破了传统以人为中心的主客体的二元关系,体现了人与自然的相融、相通,以及对自然的尊重,渗透着一种浓郁的生态审美观。伴随着工业文明在俄罗斯的发展,他后期的诗歌中以超前的意识流露出工业化对自然美和诗意生存的破坏的忧伤,而在忧伤中他依然不忘追寻失落的家园。
关键词 叶塞宁; 诗歌; 生态批评
Searching for The Survival Mode of Human Poetry
——Study on Yesenin 's Poetry fromThe Perspective of Ecological Criticism
Ma Fenying
Abstract Yesenin is Russia outstanding poet in the 1910-20s. Critics more positioned him for the Imagist poets and new peasant poet, the author think he is also a ecological poet through a close reading. His poetic world of man and nature break the traditional duality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ubject and object centered, embody the harmony of man and nature, and respect for nature, permeate with the a rich ecological aesthetic conception.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industrial civilization in the Russia, his later poetry show the sadness for the destruction of natural beauty and poetic survival, but in sorrow he still did not forget to search for the lost homeland.
Keywords Yesenin poetry ecological criticism
叶赛宁(1895~1925)是20世纪一二十年代俄罗斯杰出的诗人,他充满悲剧的一生虽如彗星般短暂,却富有诗意。他在俄罗斯诗歌史上的地位经历了历史的考验,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他重新占有了俄罗斯诗歌史上举足轻重的位置。他的诗作中浓郁的民族诗性和高度个性化的艺术创新使他在20世纪俄罗斯诗坛上闪发着耀眼的异彩。
评论界更多将叶塞宁定位为“意象派”诗人,“新农民诗人”,细读他的诗歌就会发现他也是一位生态诗人,他在世界生态文学中的地位也应该是崇高的。这位“天才的乡村歌手”,在他短暂而辉煌的生命旅程和诗歌创作中,抒写了大量歌颂俄罗斯乡村生活和大地优美景色的抒情诗,展示了人与自然和谐平等的生态画卷。徜徉于静穆、浪漫和迷人的叶赛宁田园诗境中,俄罗斯大地幽蓝而神秘、灵动而和谐的意象与情韵,无不以独特的魅力感染着我们。
但值得注意的是,叶塞宁的诗歌世界中对自然田园的抒写不是站在人是主体、自然是客体的截然二元对立的立场上的,他诗歌中的人与自然的关系颠覆了传统以人为中心的主体、客体的二元关系,人与自然,人与物是一种主体间际关系,体现了人与自然的相融、相通,平等,以及对自然的尊重,渗透着一种浓郁的生态审美观。而伴随着工业文明在俄罗斯的发展,他后期的诗歌中以超前的意识流露出工业化对自然美和诗意生存的破坏的忧伤,而在忧伤中他依然不忘追寻失落的家园。笔者拟从叶塞宁诗歌中表现出的生态审美,对工业化的忧虑,对失落家园的追寻三个方面来论证叶塞宁作为一位生态诗人的重要地位。
一、生态审美:同一个自然母亲的孩子
所谓“生态的审美首先是对自然的审美,但是这种审美既不是将具体的审美经验抽象成形而上的理性认识,也不是通过具体的审美对象来表达或对应审美者的思想情绪或人格力量。较之传统的审美,生态的审美突出的是自然审美对象,而不是突出审美者。审美者感知自然,与审美对象建立的交互主体性的关系,而不是主体与客体的关系。”[1](42)
在中外文学史上,抒写自然田园的诗歌与诗人不胜枚举,但是很多诗人仅仅是将自然田园作为自己情感的寄托对象,融情于景。也就是说并不是每一位诗人在面对书写对象时能将审美对象作为一个独立的主体,而往往更加突出审美者诗人自己。众所周知,在叶塞宁的诗歌中,最富魅力的诗是描写自然和农村田园的抒情诗,在这些诗歌中,诗人叶塞宁对自然万物的描写则完全体现了一种生态审美。
“仿佛系上了洁白的头巾的覆盖雪花的青松” [2](39)(《新雪》), “奏着催眠小调的松涛齐鸣的毛茸茸的针叶林松”[2](11)(《寒冬在歌唱,又像在呼寻》),“湖面上织出了红霞的锦衣”[2](17)(《湖面上织出了红霞的锦衣》),“闪着晶亮的雪花的白桦”[2](33)(《白桦》),“轻轻的歌唱的溪水”[2](27)(《夜》), “用晶亮的珠母盛妆打扮的一簇簇荨麻”[2(41)](《早安》),“在浅蓝的草地上游逛的新月”, [2](63)“玫瑰般的天和白鸽似的云” [2](65)(《在一抹暗淡的林梢背后》),“悬挂在那频频点头的牛的嘴唇”的“柔声呻吟的大麦秸”[2](73)(《大路把红色的黄昏怀想》),“仿佛套进了我们雪橇”的像匹马驹的“棕黄的月亮”[2](89)(《田野收割尽,小树林裸着身)……我们可以在叶塞宁的诗中无限追踪到这样“活”的自然,它们具有灵魂,和人类一样具有鲜活的生命,组成了一幅美不胜收而又和谐一体的生态画卷。
诗人用浓烈的诗情描绘和歌颂了自然中的万事万物,他的诗歌世界中的自然不是诗人情感的对应物,也不是诗人情感的映现,而是和诗人一样具有主体性的生命。诗人在诗中写道:花儿啊/我怎能不爱你们?/让咱们以你我相称/干掉此杯。以你我相称,诗人与自然破除了主体和客体的二元论关系,实现了一种交互主体性的世界。破除了人类中心主义、自我中心主义和主体客体二元论,诗人与自然就实现了一种主体间际关系,而不是主体与客体的关系。在叶塞宁歌颂自然田园的诗歌中,诗人旨在具体的感受和表现自然和田园本身的美,而不是突出诗人自己,彰显了极具个性的诗歌特色。
对诗人来说,自然万物不仅具有独立的主体性,还是他心心相印的朋友:“母牛同我侃侃谈心,/用点头示意的语言。/一片芬芳的阔叶树林,/用树枝唤我来到河边。”[2](53)(《我是牧人;我的宫殿》)“我口中吐出忧伤的话儿,/像树木悄然落下了叶子”[2](155)(《金色的小树林不再说话了》);“夜莺啊,你为什么忧愁?”/“狂风呵,请给朋友捎个信”、“吉姆,伸出爪子来祝我好运”……“金黄色的树林说话了,/用白桦树欢快的语言”。《早安》中写道:“金色的星辰眨着惺忪的睡眼,/涟漪漾起在明镜似的水面,/晨曦遍洒一个又一个河湾,也抹红了那垂网般的穹天。睡梦初醒的小白桦微微一笑,/晨风撩乱它那丝样的发辫。/嫩绿的花絮发出瑟瑟的喧嚣,/泛着银光的露珠连连忽闪。篱笆旁丛生着一簇簇荨麻,/它用晶亮的珠母盛装打扮,/还摇晃身体淘气地低声说话:/‘你好啊,祝你早安!’”[2](41)诗人与自然、诗人与物就像是亲密的朋友,彼此应和,彼此温暖,彼此相融。这种化于浓血的情结,源自诗人对生活的深切体验,源自对俄罗斯乡村生活的细致观察,源自对纯朴、静穆和神秘大自然痴迷的热爱,更源自于诗人对一草一物的尊重和对生命的体悟。叶塞宁把他的爱投向了俄罗斯的大自然,投向了故乡的一草一木,也投向了动物。这种“兄弟般的爱”已经超出了人与人之间的界限,而延伸到人与自然,人与动物。
他那首有名的《狗之歌》中,充分体现了诗人对动物主体的爱与尊重。狗妈妈生了七只狗崽,它像人类世界的母亲一样对自己初生的孩子充满了温柔的母爱:“母狗伸出舌头,抚爱狗崽/一直舔梳到傍晚,/它那暖融融的肚皮下,/流淌着乳汁雪一样白。”七只狗崽被狠心的主人装进麻袋扔进了河里。狗妈妈竭力想寻回自己的孩子,但是它的孩子再也回不来了,对这一轮月亮,它认为是自己的一个孩子,以狂吠表达着自己的思子之情,它最终只能发出悲伤的哀号:“母狗精疲力竭地爬回来,/边爬还把两肋的汗水舔,/它将农舍上空的一轮月亮/认作是自己的一只狗崽。 它凝望着蓝幽幽的天空,/大声地狂吠,哀号不休;/可纤细的月亮滑动着/隐入山岗背后的田野。”[3](240)
这首诗歌读来感人至深,母狗失去孩子的悲怆和哀怨足以令人落泪。之所以有这样的美学效果,就在于诗人并没有把狗仅仅当作和人类相对的动物,或仅仅作为自己情感的对应物或象征物,而是把狗当作一个独立的个体,一个和人一样有着自我情感和灵魂的独立主体,于是在诗人笔下母狗和人类母亲具有了一样的心理内涵。正是因为诗人对狗的主体性的承认,所以他才能充分理解狗的痛苦与困境。在这首诗中,诗人作为人类主体与狗这个非人类主体处于一种平等的位置,诗人与狗就实现了一种主体间际交流,人与自然的交互主体性得以真正实现,这也正是诗人生态审美的表现,体现了诗人的生态思想。“生态的审美是与自然交融的审美,审美者与自然融为一体,把自然物当做自己的朋友和生活伴侣,而绝对不高高在上地或远远地从外部审视他们”。[1](219)
叶塞宁几乎每首涉及到动物的诗中都体现着这种生态审美,体现着人与动物之间兄弟般的爱。《农舍里》这首诗描写了猫和公鸡温馨甜美的人性化生活图景——“老公猫悄悄溜近陶罐,/去偷喝冒热气的牛奶。公鸡在院子里唱起歌,/像给和谐的弥撒伴奏。”[2](45)田野中的奶牛陷入忧伤,因为想起了自己的孩子,那只“四蹄雪白的小牛犊”(《奶牛》)。小狗吉姆通晓人意,诗人似乎与吉姆心灵相通,于是,吉姆成为“我”倾诉衷肠的最好听众, “吉姆,伸出爪子来祝我好运,/”[2]( 271)(《致卡恰诺夫的狗》);寒冬里,“一群贪玩的家雀飞来/宛如孤苦伶仃的小孩,/在窗前紧相偎靠。/……小鸟们做了一个梦:/眼前是明媚的春美人,/浴着太阳的微笑。”[2](11-13)(《寒冬在歌唱,又像在呼寻》在最为普通的农村日常生活画面中,小动物和老母亲一起占据着主角的位置:“朝缝里正钻进几只蟑螂,……老公猫悄悄溜近陶罐,/去偷喝冒热气的牛奶。/不安的母鸡咯咯叫着,/…公鸡在院子里唱起歌,/…在那开向穿堂的窗户口,/挤着几只毛茸茸的小狗,……。”[2](45-47)(《农舍里》)
这是多么美好的人与动物和谐相处图。在叶塞宁的诗歌世界中,动物并未被对象化或工具化,它们不是诗人情感世界和人格特征的工具,相反,诗人自己似乎回归了人的自然天性,像孩子一样感受着这个新鲜而美丽的世界,成为一位自然之子。 “叶塞宁独特艺术世界的统一性表现在:在这个世界中,所有存在物都有了心灵:人、动物、植物、星球和物体——他们都是同一个自然母亲的孩子。”[4](171)这就是叶赛宁诗歌世界中的生态整体,人、动物、植物、星球和物体都是自然的一部分,都是自然的孩子,人不是高高在上的,不是自然的中心,人和自然的其他孩子一样,只是组成自然的一个部分,这些孩子一起共同丰富着自然的内涵,在这个共同的家园里和谐共存,彼此相融。叶塞宁从来都是把大自然中的万事万物看成有生命的个体,他们之间没有隔膜,没有距离,所以他才可以那么肆意地亲近大自然,那么挥洒自如地任情感汪洋,和生命对话。
二、对工业化的忧虑:向原野的喉头伸出魔掌
城市生活中的叶塞宁一度放纵、酗酒、打架斗殴,表现在他的诗歌世界中,宁静优美的大自然不见了,代之以城市弯弯曲曲的街道。但是叶塞宁对田园和自然的情愫就像他身体里涌动的血液,即使在城市生活中,他依然保留着对大自然和动物的眷恋,只是这时诗歌世界中的自然已经被蒙上了一层忧伤的回忆的迷雾。
叶塞宁一生虽然短暂,但是却经历了复杂的时代。他个人的命运似乎被套进了历史的车轮。革命、阶级斗争、新政权的建立,这一切无不影响着敏感的诗人,影响着他对人与自然、城市与农村关系的感知。在革命的洪流中,叶赛宁怀着乌托邦的理想歌颂革命,幻想有一个“庄稼汉的天堂”。他那些强烈表现革命热情的作品,如《铁匠》、《天上的鼓手》、《同志》、《如歌的召唤》等诗,在一定程度上脱离了诗人的感伤基调,但却是诗人诗歌中革命旋律的起点。残酷的阶级斗争使他从“使普天下和解”的美梦中惊醒过来,而从城市里来的不速之客“铁的客人”,给了他乡村将蒙难的不祥预感,他感觉到了新的工业文明的发展对大自然农村美好田园的冲击和侵蚀,作为乡村象征的“泥罐子”在城市“铁罐子”上碰得粉碎。一度充满革命激情的叶塞宁坠入了精神危机深渊,在惆怅之余他曾与文坛一些名士结交,出没于莫斯科小酒馆,借酒浇愁,吟诗遣闷。《莫斯科酒馆之音》表达的就是诗人在城乡关系上的迷茫之情。而正是这种情绪使他成为一个因心爱“乡村罗斯”的逝去而无奈、无望和无情的无赖汉形象。
苏维埃的建立使俄罗斯的农村开始发生巨大变化,但是叶赛宁并没有迎来之前他想象中的农民的“天堂”,反而看见了农村经济的凋敝和田园诗意美的丧失。在早期苏维埃人的社会理想中,最为关键的是技术的极大进步,以及随之而来的物质的极大丰富。“在这样的理想国中,工业、城市才是中心,大自然和农村被推到了一个次要的位置。列宁曾用一个公式表达了这一理想:共产主义=苏维埃政权+电气化,而电气化就是工业化。” “这样,农村连同它所附带的一切传统和价值观念注定被取代,注定被抛弃。” [5](87)列宁曾经指出,俄国没有工业,就不能维持独立国家的地位。所以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政策指导下,不到20年的时间,俄罗斯就飞速的完成了从农业大国向工业大国的转变。在这一过程中,对农村的掠夺和破坏十分严重,对自然环境的过度开发利用也对日后苏联的生态危机埋下了隐患。
叶赛宁在晚期诗作中对铁路和火车的描写就表达着他对工业化所导致的自然美的消失和灾难性污染的忧虑和恐惧。在《库里科夫原野》里叶赛宁写道:“吹吧,吹吧,灾难的号角!/怎么办,我们现在该怎么办,/在这肮脏不堪的铁轨上?/霜雪就像石灰一样,/抹白这村庄和草场。/你们再无处逃离敌手,/你们再无处躲避祸殃。/瞧它,正腆着铁的肚子,/向原野的喉头伸出魔掌。”[6](164)《走出彼得霍夫森林》则把林边铁路喻为囚困森林的牢笼:“(铁轨)泛着白光刺入视野,/枕木和砾石咯吱作响,/迎接着即将碾过的巨大轰鸣。/静默的森林无奈地矗立,/注视着眼前无法突破的牢笼。”《复活节狂想》进而描写铁路所经之处油污遍地、狼藉不堪的场景:“铁轨探着它坚硬的触须,/蜿蜒着身子拱进森林。/青草和野花在黏稠的油污里挣扎,/林中白烟缭绕,/不知是雾霭还是机车喷吐的蒸汽。”
叶赛宁认为,铁路的铺就使得工业文明的触角延伸至俄罗斯的每一处偏僻角落,火车“正腆着铁的肚子,/向原野的喉头伸出魔掌。”静穆、惬意、和谐的诗意田园被破坏了,“青草和野花在黏稠的油污里挣扎,/林中白烟缭绕,” 俄罗斯大地上被工业化的油污所污染,连青草、野花也未幸免于难。那个幽蓝而神秘、灵动而和谐的俄罗斯大地失落了。伴随着铁路的铺就,自然资源的流动速度加快,从而导致人类对自然界的疯狂掠夺更加肆无忌惮,物质欲望加剧恶性膨胀。铁路由鼎沸、喧嚣的城市伸展到宁静、和谐的乡村田园,沿途播撒的是噪声、污染和掠劫。铁路剥离了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使诗意的生存一去不复返了。
我们都知道,铁路是“现代工业的先驱”,是现代工业文明的标志,在俄国的工业革命中,铁路的建设及其作用是不容小觑的,因为商品性农业的发展和工业品销售市场的扩大,工业发展所需劳动力能否得到最大满足,都取决于铁路网的发展程度。19世纪60年代,俄国的统治者真正意识到修建铁路的重大意义,视修建铁路为发展经济的首要任务。于是,1861年改革后,俄国铁路线的长度逐年成倍增长。19世纪的俄国铁路建设经历了两大高涨期: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以及90年代后半期。从1865年到1875年,俄国铁路网平均每年增加1500公里,到19世纪80年代,俄国已经建立了以莫斯科为中心的许多支线的铁路网络。铁路的建设为俄国经济的发展注入了血液,打通了经脉,催生了19世纪末俄国工业的高涨。20世纪初,伴随着苏维埃政权的建立,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时代氛围中,人们开始为钢铁和机器唱起了雄壮的赞歌,而我们在叶塞宁的诗歌中却发现了铁路的“丑陋”,于是诗人发出了质问:“怎么办,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在这肮脏不堪的铁轨上?” 在叶塞宁笔下,以铁路和火车为代表的工业文明的到来给人类吹响了灾难的号角,铁轨是肮脏不堪的,原野再也无法躲避火车带来的祸殃,火车就像一个工业巨人,发出巨大的轰鸣,吞噬着田园和自然的静穆、诗意。诗人用诗歌抒写着以铁路为代表的工业文明对自然田园的破坏和侵蚀,流露出工业化对自然美和诗意生存的破坏的忧伤,这无疑表现了一位生态诗人的前瞻性眼光。
三、波斯抒情:诗意家园的追寻
在早期苏维埃文化中,庸俗唯物主义思潮盛行一时。“钢铁和机器的颂歌”成为时代的主旋律。在这种时代氛围中,大自然存在的目的只能是服务于城市化和工业化,是被征服、被改造、被掠夺的对象。相对于城市和工业,农村自然不可避免的带上了消极的、负面的色彩,不再适合作为诗意讴歌的对象。在这种大的时代背景下,叶塞宁的诗歌中出现了“失落的家园”主题。1919年的《我是乡村最后一名诗人》里,叶塞宁表达了对乡村家园失落的伤感:
我是乡村最后一名诗人,
我在诗中赞美简陋的木桥。
我置身落叶缤纷的白桦丛,
参加它们告别的祈祷。
这蜡烛是血肉之躯制成,
在金色的火焰中逐渐燃尽;
月亮如同挂钟一样呆板,
敲响喑哑的午夜十二点。
在蔚蓝色的田野小道上,
不久将出现一个铁的客人。
他伸出黑漆漆的手掌,
把洒满霞光的燕麦割尽。
这是一些无生命的手掌,
有了它们,我的歌就无法生存!
只有那马鬃一样的燕麦,
还在为旧日的主人伤心。
风儿跳起追荐亡灵的舞蹈,
希望淹没燕麦的悲鸣,
呵,呆板的挂钟,快了,快了!
敲响喑哑的午夜十二点钟。[3](248-249)
在这首诗中,“简陋的木桥”成为古朴的俄罗斯乡村的象征,那是诗人一直挚爱的土地。诗人“在诗歌中赞美简陋的木桥”,但是如今工业文明的巨大轰鸣正在堙没俄罗斯乡村的美好,诗人忧伤地注意到悲剧正在自己脚下蔓延。于是,诗人在落叶缤纷的时节作为大自然的客人、白桦的朋友,受它们之邀来为它们送别,为它们祈祷。在这沉寂的夜里,唯有月亮陪伴着诗人。诗人把月亮比喻成挂钟,一方面,月亮是俄罗斯乡村的守望者,陪着诗人一起见证最后的乡村;另一方面,月亮即将敲响的钟声既是午夜的钟声,又是“我”生命的丧钟。诗人意识到自己也许会随着这最后的乡村一同消逝。
“铁的客人”象征以铁路为代表的城市化和工业化,那“洒满霞光的燕麦”终将被工业铁爪吞噬,徒留诗人独自屹立在即将消隐的田野里一遍遍地为“庄稼汉的天堂”唱哀歌。 “铁的客人”有着“无生命的手掌”,不仅是乡村与城市、农业与工业之间天生的不可调和的矛盾,而且诗人自己诗歌与城市工业之间的抗拒。诗的命运与乡村命运休戚相关,乡村的毁灭即是诗歌的毁灭。大自然是叶赛宁诗歌的天然养料,俄罗斯乡村是他诗歌的精神寄托。当有一天,大自然以及乡村遭到破坏后,叶赛宁深知自己的诗歌也将走向末路。
“风儿跳起追荐亡灵的舞蹈,希望淹没燕麦的悲鸣,”其中“风儿”象征主张工业化城市化的人,“跳起追荐的舞蹈”即他们对于工业文明的推崇。 “我”为俄罗斯乡村所唱的哀歌终究抵挡不过革命者为工业文明所唱的赞歌,“我”的歌声只能被湮没。
对于叶塞宁来说,乡村的家园已经无法回去,而城市里又无法放置诗人的灵魂。城市“楼房的骨架”,“颤抖的灯笼”,“莫斯科弯弯曲曲的街道”根本就不可能成为“家园”,因为这些冰冷怪异,无法温暖心灵。“像穿上疯人院的紧身衣/我们把天性浇进混凝土”[7](61)(我还从不曾这样的疲乏,1923)。 “乡村,乡村有生活,而城市……这种谈话令我感到沉重。它压抑着我。” [8] (317-318)
在白银时代,叶赛宁以其诗人特有的敏锐预见到现代文明对生态文明的毁灭性冲击,他一度沉沦在黑色的忧伤中不能自拔,因为往日的那个美好家园似乎已经不在,美好的田园被“铁的客人”吞噬,但是可贵的是,叶塞宁在忧郁中依然苦苦追寻那个失落的家园。
在叶塞宁生命最后的时光中,他完成了《波斯抒情组诗》(1924-1925)。诗人似乎从黑色的忧郁中解脱出来,重新追寻着蓝色的俄罗斯家园。“我那旧日的伤痛平复了,/酒疯吞噬不了我的心房”[2](167)(《我那旧日的伤痛平复了》)诗人又开始拿笔抒写着“澄澈蔚蓝的天空”、“鲜花盛开的林间”[2](185)(《空气是如此澄澈和蔚蓝》)“浮动着玫瑰的暗香”(2)(181)的田野(《番红花的国度里暮色苍茫》)……,但是细细品读这些诗就会发现,诗人笔下的波斯虽然热情浪漫、色调富丽,但是在一景一物的描写中依然有一种挥之不去的忧伤。波斯虽美好也是异邦,诗人心中魂牵梦萦的依然是那个遥远的故乡:“波斯啊,我知道你美好异常。/玫瑰花像灯盏一样绽放,/它们那清新矫健的姿影/又使我想起遥远的故乡”[2](193)。(《菲尔多西浅蓝色的祖邦》)“如今我该返回俄罗斯去。/波斯啊,竟然我要离开你?/出于对故乡的深情眷恋,/我竟然要永远和你分离?”[2](191)(《霍拉桑有这样一家门户》)诗人应该返回的俄罗斯不是城市的俄罗斯,而是那个长满白桦的俄罗斯原野——俄罗斯乡村。众所周知,叶塞宁一生并未去过波斯,《波斯组诗》的创作可以被理解为诗人向幻想的跃进。诗人借助波斯这个意象,表达了自己对诗意家园的追寻。《波斯组诗》创作于诗人生命的最后阶段,这绚烂想象力的爆发向我们透露了作者内心深处对诗意生存模式的执着和眷恋。
四、结语:我能把大地的语言领悟
俄国1861年农奴制改革之后,经济突飞猛进的发展,俄国开始进入工业化时代,到19世纪末,俄国基本完成工业革命,石油和机器制造产业发展很快,到19世纪末铁路里程已经达到5.2万公里,铁路交通网基本形成。但是,十月革命前,俄国依然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工业产品只占国家全部产品的l/3,农业产品则占国家全部产品的2/3。1914年沙俄的工业产品只占世界工业产量的2.46%。1917年11月7日,俄国人民在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领导下,取得了十月革命的胜利,1917年11月~1918年3月,全国各地相继建立了苏维埃政权。苏维埃政权建立后,苏维埃俄国党和政府所面临的首要任务,就是恢复被破坏了的国民经济。要使新生的苏维埃俄国彻底“摆脱资本桎梏的整个解放事业的成功和社会主义的胜利”就必须“大大提高社会生产力”,实现工业化和农业机械化。正是在这种背景下, “钢铁和机器的颂歌”成为早期苏维埃文化中的时代主旋律。但是我们从叶塞宁晚期的的诗作中并没有读到这种主旋律,相反,我们看到的是他对工业文明的发展对田园诗意破坏的忧虑和忧伤。他没有对工业文明的发展带来的物质巨变而歌唱,而是依然执著于讴歌自然田园之美,同时在他后期的诗歌流露出对铁路为代表的工业文明对自然田园造成的破坏的恐惧和痛心,他以超前的意识表达了工业化对自然美和诗意生存的破坏的忧伤,但是,可贵的是,诗人在忧伤中依然执着于追寻失落家园的追寻。
叶赛宁在《心灵将天庭苦苦思念》中写道:“我能把大地的语言领悟,却无法抖落大地的痛苦。”他的一生都在用大地的语言为大地歌唱,也在为大地的痛苦而痛苦。大地的痛苦就像生长在他身体上的瘤,已成为他生命的一部分,他们的痛苦是相互依存的。他终其三十岁的一生始终不渝的眷恋着乡村的一切,因此人们把它称作“逝去的乡村歌手”,他自己也在诗中称自己是“乡村最后一名诗人”。他因为致力于对未经过工业文明污染的田园、农村的歌颂一度受到时代的误解和世人的嘲笑,但是在世界生态面临巨大危机的今天,我们发现叶塞宁诗歌中素朴、纯净,闪耀着蔚蓝色的美的俄罗斯乡村和人与自然、人与动物宁静、和谐生态画卷却成为我们追寻的家园之梦,也是我们梦中追寻的诗意生存模式。在二十世纪的初期,叶塞宁就预见到了工业文明会对生态带来的巨大影响,同时在诗作中表达着诗人对工业化所导致的自然美的消失和灾难性污染的忧虑和恐惧,所以说叶塞宁在世界生态文学中崇高的地位是不可动摇的。
参考文献:
[1]王诺:欧美生态批评:生态学研究概论[M],学林出版社,2008。
[2][俄]叶赛宁:叶塞宁诗选[M],张建华主编,顾蕴璞译,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6。
[3]俄罗斯白银时代诗选[M],汪剑钊译,云南人民出版社,1998。
[4][俄]阿格诺索夫:20世纪俄罗斯文学[M],凌建侯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
[5]周湘鲁:俄罗斯生态文学[M],学林出版社,2009。
[6]吴泽霖:叶塞宁评传[M],浙江文艺出版社,1999。
[7][俄]叶赛宁:叶赛宁诗选[M],郑铮译,北京:外国文学出版社,1991。
[8][俄] 阿格诺索夫:白银时代俄国文学[M],石国雄、王加兴译,译林出版社,2001。
 最新评论
最新评论|
版权所有© 中外文学研究课题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