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版权所有© 中外文学研究课题组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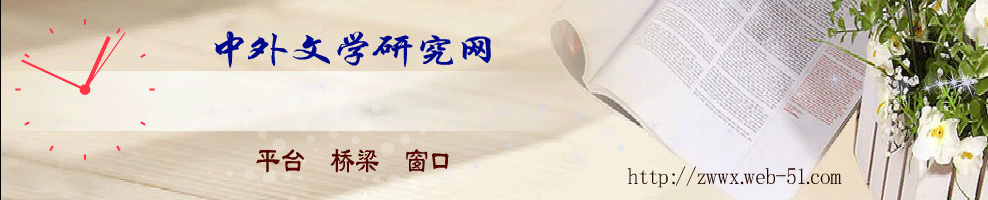
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 比较文学专业 王梓涵
【摘要】莎士比亚作为人类文化史与文学史中,最著名的剧作家,在他的一生中留下了诸多享誉世界、广为流传的戏剧作品。莎士比亚不仅作为英国文化的符号与代表,而且作为对人性的深广度思考的历史范本,成为人类思想文化史中一抹永不褪色的经典。时至今日,莎士比亚的剧作在世界各大剧院中仍不断地上演着,被赋予着新的内涵与意义。本文以电影《麦克白》为对象,参照原著《麦克白》,在对比分析中运用现代心理学的理论,以一种精神创伤机制为新的切入视角,探究麦克白悲剧的成因,以及莎翁创作中的虚无主义。
【关键词】潜意识;创伤后应激障碍;欲望;虚无主义
莎士比亚参照史书,用他的历史剧,书写下了英国历史中光辉与黑暗并存的一页页,书写着英国历史上君王的更迭与王朝的兴衰,以及作为君主的人所度过的短暂一生。莎士比亚笔下的君王,以个体的人的存在形式,呈现着他们既作为王朝统治者,又作为具有个性与个体价值的人的多面形象。归根结底,莎士比亚历史剧中的君王,是以作为个体的人的形态,而非作为君主这一符号而存在着的。他们首先是人,其次才是英格兰,乃至英伦三岛的王权统治者。他们被赋予了国家、责任、权力,终生被君权、国家、人民所束缚。因此,从出身来看,他们的存在就已经具有了悲剧的二重性,既作为个体的人的存在悲剧,又作为国家实际统治者的君王的身份悲剧。
然而,作为莎翁四大悲剧之一的《麦克白》,虽非英格兰的君王,却因女巫的预言,走上了王权争夺的阴谋与战争。作为一个历史上曾经存在过的苏格兰君王[1],他不断经历着个体的存在悲剧,命运悲剧,身份悲剧。究竟是麦克白自己的野心与权欲,还是麦克白夫人的野心、权欲与教唆,还是有其他隐秘而强大的力量,或者是暂且未知的心理动因,促使着麦克白最终走向弑君篡位,暴虐滥杀,充满荆棘与鲜血的王座?本文借助对电影版本与原著剧本的《麦克白》的分析,一一来探究麦克白成王之路的种种悲剧背后的原因。
一、 王冠、王者与英雄
通向无上权力的宝座之路,古往今来,遍寻古今中外的历史典籍,无一不是充满着阴谋的政治博弈与血腥的政治斗争。王冠与王座始终染就着失败者与牺牲者的鲜血,是权力的游戏最终的战利品与个人欲望的终点。在英国的王朝历史中,帝王的更迭交织着家族与权贵的利益、荣誉。每一个王朝的兴衰都代表着一个家族的兴衰。而成为上位者的王位继承人,不仅面临着成为众矢之的,而被图谋王位的阴谋家所暗杀的命运,而且还面临着来自家族内部、朝臣、他国王室等等不可预知的威胁。随时都会丧命,被暗杀,被斩首,被废黜,被无理由的放逐,流亡国外,被终身幽禁在伦敦塔,惨死其中。尽管面对如此种种可怕的结果,但仍要参与到权力的游戏中,与命运博弈,与他人博弈。直到头戴王冠,受到加冕,登上统治者的王座,掌控着巨大的权力。权力就像历史前进着的坚固车轮,无情地碾压着渴求得到权力的人的灵魂与肉体,使他们前赴后继地成为权力与野心的牺牲者。
伊丽莎白一世统治时期,虽然开创了被后世誉为英国历史中最光辉的黄金时代。但在这位女王即位前,却曾遭受过被人监视,囚禁伦敦塔,险被自己同父异母的姐姐玛丽王后处死的经历。而在她即位后,王权争夺的风波也从未停息过。被亲信的大臣背叛,被国内的天主教徒联合外国势力、教会势力暗杀,与西班牙王室敌对,对王位继承权正当性的污蔑,被国内激进的清教徒、人民,与争取独立的叛军所威胁。伊丽莎白一世的王位岌岌可危,她随时都会重返伦敦塔,命丧断头台。因此,在莎士比亚笔下的君王中,随处可见的是一种缘自对丧失王权、丧失性命的恐惧的焦虑情绪。尤其是那些通过弑君篡权而夺得王位与统治权的君王,他们更是惶惶不可终日,多疑多思,恐惧不安,时刻陷入对王位占有的焦虑情绪中。比如,亨利四世,哈姆雷特的叔叔,麦克白。其中,弑君者远比废黜君王者更恐惧篡权失败后的结果。因为,在中世纪王权思想与政治实践中,弑君者要远比废黜君王者承受着更大、更严酷的刑罚。枭首示众族灭后,世代都要承受着弑君者的污名而留存于历史,被世人唾骂鄙弃。这不但是对于肉体的瞬间毁灭的惩罚,更是一种在精神层面上持续不断的,延续着的惩罚。
身处王权统治时代中的麦克白,不会不知道弑君的下场与后果。但他在战胜叛军归来后,在成为受到国王嘉奖与荣誉恩赐的英雄后,仍做出了弑君的举动。除却三女巫预言的外在因素,是否在他心中还存在着一些不可告人的阴暗欲望与政治野心。而对这一内在因素的探求,在《麦克白》诸多不同形式的演绎版本中,饰演麦克白的演员们似乎给出了他们的答案[2]。英国皇家莎士比亚环球剧院、纽约大都会歌剧院曾参演过麦克白的男主角们,以及一些研究学者认为,麦克白悲剧的原因在于三女巫预言中所带来的不可抗拒的宿命,以及他的妻子麦克白夫人的蛊惑与调唆,深爱妻子的麦克白为了达成妻子的野心与愿望,而做出了弑君篡位的可怕行为。不难看出,这一理解中推卸罪责,摆脱罪恶感,带有性别歧视的男权传统思想的偏见与谬误。事实上,问题的根源出自麦克白自身。
麦克白以勇猛击杀叛军首领的英雄身份出场,而不是一个拥有王位继承人顺序的王公贵族。在剧本第一幕第二场中,通过军曹的寥寥数语,便刻画出了麦克白的英雄形象,但却就此带过了对战场具体情状的细节描写与说明。然而,在电影中,导演借助光影,用特殊的拍摄手法,呈现出一幕幕惨烈、血腥的冷兵器战斗场景,以及战斗在这一残酷战场中的麦克白形象。电影的画面直观性为观众带来了强烈的视觉冲击。电影中战场上的尸横遍野,残肢断臂,种种非正常的死亡方式,都以画面的形式直接冲击着观众的感官与神经,带来心理上的震撼。虽然莎士比亚并未对战争场面作细致的描写,但可以想象到的是置身其中,冲锋陷阵、奋勇击杀叛军的麦克白,当时所面临的种种来自外界的感官刺激与心理震撼。麦克白不断地经历着同伴在他面前的迅速死去。生死的界限在战场被模糊,死亡的阴影被扩大,战场中所经历的一切成了麦克白心中挥之不去的心理创伤与决定性事件[3]。可以说,从战场归来后,作为获得爵位的英雄麦克白,患上了战争创伤后应激障碍[4]。而这一心理疾病及其临床表现,成了麦克白弑君篡位这一行为过程中的部分心理动因与生理表现。
战争创伤后应激障碍作为创伤后应激障碍的一种[5]。在战争频繁成为人类用来表达思想,宣泄不满与沟通交流的实用工具后,迅速成为现代社会中军人群体频频爆发的心理疾病。这一疾病对个人,对他人,对社会的危害性极大,而患病后患者行为的危险性更是不可估测。伊拉克战争后,美国社会中患有此病的大量伤兵和退役军人,成为了暴力犯罪与持枪犯罪的主要构成者。其中,患有此症的连环枪击案的凶手比例,与美国本土恐怖主义、反社会性枪击案凶手的比例不相上下。在这一现代性的解读下,麦克白的种种行为与性格、心理的转变,便有据可循,有理可依了。
麦克白凯旋的路上遇到了带来预言的三女巫。比起班柯的怀疑,麦克白率先选择了相信预言,并在受到预言中所说的封爵后,期待着更大的尊荣。在麦克白的旁白中,他对权力的渴望与野心可见一斑。“两句话已经被证实,这就像美妙的开场白,接下去堂皇的帝王戏就要正式开演。”[6]麦克白充满期待地盼望着预言的实现,“想象中的恐怖远过于实际上的恐怖,我的思想中不过偶然浮起了杀人的妄念,就已经使我全身震撼,心灵在猜测之中丧失了作用,把虚无的幻影认为真实了。”[7]而他这种毫不掩饰权欲的野心,使得麦克白内心深藏着的,不被君臣纲常与政治伦理所宽宥容许的权欲渴求,当面对成为麦克白的心理触发机制的,且具有超现实主义色彩的女巫预言时,便在外化为言语的预言刺激下,触发了麦克白心中长期被理性、伦理与社会规约,压抑、束缚着的对王权无限渴求的深层欲望,将这一隐秘的潜意识思想释放到意识中。即使,麦克白对弑君篡位深感恐惧,为之战栗,甚至将虚幻当作真实。但仍说明了麦克白在潜意识中是有着弑君篡位的冲动的,并且因为预想弑君而在一瞬间获得了潜意识的欲望满足。对弑君篡位的可怕后果,违逆伦理纲常与理性的惩罚的忧虑,都不及一次在想象界中潜意识的满足所带来的快乐。简言之,是麦克白自己早已有了弑君篡位的野心与权欲。同时,也因他所患的战争创伤后应激障碍,将权欲的野心与弑君篡位的潜意识冲动,渗透进他已经产生功能障碍的意识中。因此,麦克白才会在备受心理疾病折磨的极端处境中,强烈而明显地挣扎在释放潜意识与压抑潜意识的矛盾边缘。而麦克白内心的战场使得他的行为更具戏剧冲突性,也使得他的形象与命运的悲剧性更加突出,更加强烈。
弗洛伊德以潜意识为基础的人格学说,为分析麦克白的悲剧成因提供了一种理论方法,而战争创伤后应激障碍却为此提供了一种心理学依据。在弗洛伊德本能学说的晚期理论中,提出了人的死亡本能一说。死亡本能向内则表现为受挫后退回自我内部的自毁、反抗等心理,向外则表现为征服、侵犯、毁灭他人等心理。而麦克白渐渐变得狂躁、暴虐、残忍、多疑,正是他的死亡本能通过创伤后应激障碍的心理机制,以行为、言语的方式来一一呈现的。剧本中莎翁用大量的旁白与梦境,来突出刻画麦克白内心与性格的转变,而在电影中则运用了慢镜头和场景闪回,以一种阴郁迷幻的色调表现着麦克白急剧变化的精神世界。从创伤后应激障碍的临床表现来看,患者会出现创伤性再体验的症状,主要表现为思维、记忆或梦境的不断反复,不自主地涌现与创伤有关的情境或内容,出现严重的触景生情反应,甚至,感受到创伤性事件的重现。因此,在电影中麦克白不断看到战场情景,以及女巫的多次出现。从杀害邓肯那一刻起到谋杀班柯,再到滥杀无辜直至战死的过程中,逐渐出现在麦克白眼前的错觉、幻觉,以及分离性的闪回事件,使他精神错乱,继而表现出了攻击性行为。麦克白过度警觉,惊跳反应情绪的不断增强,使他变得焦虑、狂躁,变得越来越恐惧不安、多疑残暴。也许,一开始女巫的出现都只是麦克白的幻觉。也就是说,麦克白在凯旋途中,他的战争创伤后应激障碍就已经开始病发了。而麦克白时刻感到自己用不正当手段得到的王位会受到威胁,感到自己将会成为下一个登上断头台的,背信弃义的叛国者与弑君者而遭受极刑的心理状态就不难理解了。
从一开始,麦克白原本正常的人格,就因经历了战争的心理创伤,而变得逐渐失衡。他的本我、自我、超我在受到女巫预言的刺激下,这三者之间的关系也从原本的和谐急剧发展为矛盾、分裂愈加明显的程度。他的本我充满着无限膨胀的权欲野心,始终都涌动着弑君篡位取邓肯而代之的冲动。当预言出现时,他没有任何怀疑便相信了所说的内容。他开始有了强烈的期待,但他的理性与伦理道德思想,却又使他对邓肯尽职尽责,忠君爱国。一方面麦克白直面自己的野心,做好了弑君的准备,一方面面对主君邓肯与同僚,谦卑恭顺,隐藏着弑君篡位的欲望。这一思想上的双重性,正是麦克白人格上矛盾对立,不断分裂着的病态形式的反映。在权欲的贪念与弑君的恶念共同支配下的麦克白的心理,自归来后,便一直徘徊在满足欲望与压抑欲望间。麦克白在当时社会的君臣纲常、伦理道德、礼仪规约中所形成的超我,约束着他的自我,迫使他去顾虑英雄的名誉,顾虑弑君的后果。而他的本我却时刻在提醒着他去实践自己的权欲野心,杀了邓肯,以换来内心冲动的满足。因此,已经受到创伤的自我,在这种极端的心理矛盾处境中,急剧失衡,无法控制和压抑本我的冲动,更无法调和超我与本我间的矛盾,来运用理智系统地感知外部世界,处理内心的情感冲动。而后来麦克白的狂躁、暴虐、多疑,也正由于战争创伤后应激障碍得不到及时的治疗,以及麦克白夫人的言语刺激,使得病情不断恶化,最终导致麦克白的人格彻底混乱崩溃,继而直接表现出了他暴君的一面。
事实上,麦克白是位无权无势,没有显赫血统家世的英雄,但却渴望着头戴王冠,手拿权杖,坐在王座上成为王者的命运。他不切实际、痴心妄想的野心与权欲,扭曲了他的理智与信念。他的暴虐与滥杀,使他那自不量力的权欲野心,在他一无所有,腹背受敌时的困兽之斗,看起来更加可悲。因此,篡位的麦克白这一从战场归来后的英雄,只能成为刚愎自用、滥杀无辜的暴君,而非贤明伟大的王者。
二、麦克白夫人,成为共犯的爱情
在莎翁这部展现人类内心邪恶与贪婪等阴暗面的剧作中,麦克白所承受的悲剧命运,除了由他自身所具有的权欲野心,以及所受的战争创伤后应激障碍这一心理疾病导致外,似乎还能从他的妻子——麦克白夫人身上,找到些许关键的原因。在传统观念中,通常研究者认为作为超自然因素出场的女巫,将对权力的野心以预言的形式植入了麦克白心中,并潜移默化地影响着麦克白的精神与行为。或者认为是麦克白夫人不断地教唆、逼迫,才使得麦克白最终在麦克白夫人野心的支配下,做出了弑君篡位的举动。但通过具体的文本分析,事实上,麦克白自己的野心与不断恶化的病情,才是最终导向悲剧的主要原因。
关于对麦克白权欲与野心获得的学术讨论,不难看出,在一定程度上,是有着性别偏见意识的。研究者不约而同地站在了男权与父权制的角度,将男性犯错的借口与责任随意推卸到女性身上,甚至,让女性去承担本该由男性承担的罪责与惩罚。人类始祖之一的亚当在偷食禁果后,面对耶和华的惩罚,也发出过“要不是夏娃的话,就不会犯这样的错”[8]诸如此类推卸罪责的话。这一文化传统中对男女犯罪后责任认定的认知所带有的性别偏见,使得在对《麦克白》悲剧的思考中带上了鲜明的性别不平等意识。将麦克白弑君篡位的全责推卸到麦克白夫人身上,显然是既不公平,也毫无根据的。
然而,这并不能说明麦克白精神的错乱与弑君行为的发生,在除了他自身的内在原因外,就没有其他外在的因素。首当其冲的是麦克白夫人。作为麦克白的妻子,她是一位与麦克白有着同样强烈权欲与政治野心的女人。她的出场,一开始就注定了她只会加剧麦克白的心理创伤,注定了她必将成为麦克白弑君行为的共犯,最终成为麦克白悲剧的牺牲品的命运。但是,在不断地舞台演绎与理解中,麦克白夫人这一形象自身的负面影响被夸大,以及被女巫化、恶魔化,使得对麦克白夫人真正所起的作用,无法得出客观的分析结果。因此,忽视了麦克白夫人的悲剧性,麦克白夫妇二人真正的情感关系,以及麦克白夫人对麦克白真正的意义所在。
麦克白夫人的出场由一封麦克白写给她的家书而起。在信中,麦克白称呼自己的妻子为“我的最亲爱的有福同享的伴侣”[9],而在各个版本的演绎和电影中,都保留了这个“我的最亲爱的”称呼。可见,在麦克白心里,他的妻子占据着极其重要的地位。甚至,可以大胆猜测在麦克白心中,妻子与国家、君王、野心有着同等的地位。无疑,麦克白是深爱着自己的妻子的,是与妻子无话不谈,分享一切思想与情感的。因此,这也为日后两人共同所犯的弑君罪恶,奠定了情感基础。在莎翁诸多戏剧中,麦克白夫妇二人的爱情与婚姻关系可谓稳固异常。当莎翁笔下其他夫妻、情侣经历种种情感波折与考验时,这对夫妻却面对着共同的未来,朝着一个共同的人生目标而付出着所有。麦克白夫人知道自己的丈夫渴望得到王冠,成为王者,想要实现何种的政治野心与欲望,而且也愿意为了丈夫的理想甘愿付出,出谋划策以帮助麦克白实现他的目标。甚至,不惜亲手染血,犯下弑君的重罪,并无条件的信任麦克白,帮他在众人面前隐藏罪恶。而麦克白也一直视妻子为最亲爱的伴侣,一位能完全知道他所思所想所求,并完全理解的,甚至还能为他付出一切,支持他,鼓励他,鞭策他的女性。在麦克白看来,麦克白夫人已不仅仅只是他的人生伴侣,而更是一位能与他并肩战斗、值得信任的战友。二人心意相通,志趣相投,因此,麦克白弑君篡位的野心,从一开始就不再是他偶然因预言获得的,而是他们夫妻二人长久留存于心所共同拥有的权欲与野心。从性格上看,麦克白夫人比起麦克白,更加果敢决绝,也更有魄力手段,比男性更独断强势,也更狠毒阴险。在麦克白想要以一直以来坚守的正当手段夺权,而产生自我怀疑、否定,顾虑重重、犹豫不决的延宕时,是麦克白夫人厉声训斥着麦克白心中的“我不敢,我想要”[10],打消了麦克白的顾虑,让他彻底安心,最终实施了谋杀邓肯的行为。而且在事后,安抚了心理几近崩溃的麦克白,冷静地为他妥善处理了沾满邓肯鲜血的凶器。在这段稳固的婚姻关系中,麦克白夫人就成了麦克白的主宰,而深爱并信任妻子的麦克白,面对自己的权欲野心,以及面对内心的矛盾动摇时,无条件地选择了相信他的妻子,听从他妻子的劝说与安排,这一过程就不难理解了。麦克白夫人所说就是麦克白所想,而麦克白所做就是麦克白夫人所想。面对着弑君篡位的野心,事实上,他们二人的精神早已达到了完整的合一。麦克白夫人作为麦克白弑君的共犯帮凶,不仅通过言语加快了麦克白完成弑君的进程,实现了他的欲望,而且借帮助麦克白完成弑君这一行为,促使着麦克白最终也实现了她的欲望。可以说,麦克白夫妇间的爱情在杀死邓肯,实现篡夺王位的野心上,达到了夫妻情感相处中最和谐的境界。
再从精神分析学的角度,深入探究分析麦克白夫妇“共犯”关系的心理成因,以及在“共犯”关系中麦克白性格、心理急遽变化的原因。按照拉康的“镜像”理论,麦克白夫人是以作为建构麦克白其人及其思想的他者而存在的。因为麦克白夫人与麦克白性格、思想上的相似性,以致当麦克白面对他妻子时,都像是在面对一面镜子中的另一个自我形象。显然,麦克白夫人的形象具备了麦克白所渴望拥有的一切人格品质与精神气质。因此,麦克白才会被麦克白夫人所吸引,所深爱,进而在二者的婚姻关系中处于被主宰的地位。换句话说,是麦克白夫人这一个体的存在,使得麦克白以她为参照对象,建构了与麦克白夫人极为相似的自我与人格。同时,麦克白也将一部分自我形象的思想与情感投射在麦克白夫人身上,使之成了麦克白人格中潜在分裂着的另一人格的象征。而麦克白夫人所表现出的性格特质与思想,恰好是麦克白矛盾的内心世界中,为满足欲望而具有强烈杀戮冲动的心理所表现出的具体状态。如果说麦克白残存的理智与对谋逆行为的禁忌是压抑他内心杀戮冲动的关键,那么,麦克白夫人的言行则是开启、激发麦克白欲望的关键。因为她象征着麦克白不断变强的潜意识,而这个不受控制的潜意识也最终彻底取代了麦克白的理智。正因为麦克白建构的自我形象与麦克白夫人这一他者的形象极为相似,甚至某种程度上的一致。所以,才加剧了麦克白在经历战争所带来的精神创伤后,未愈的情况下病情反复不断加重,对自我认知也越发混乱。
象征着麦克白不断变强的潜意识的麦克白夫人,在麦克白对弑君这一行为产生怀疑与恐惧时,作为触发麦克白心理创伤的机制,通过言语的刺激,成功地将麦克白心中早已失衡的人格天平,拨向了彻底崩溃的一边。当麦克白在杀害国王邓肯后,他看到了幻象,有了幻听,瞬间的精神错乱,都在表明他病情的急剧恶化。而他妻子对权欲的野心,使得麦克白自己都没有意识到他的心理状况出了问题。或者说,由于对王权的极度渴望,而使得他们二人都丧失了理智,而没有注意到心理上发生的微妙变化。邓肯死后,麦克白夫妇都不约而同地在用水反复不断地清洗着自己的双手。在电影中,麦克白通过冷水沐浴来清洗自己。在原著剧本中,已陷入疯狂的麦克白夫人不断重复着洗掉手中血污的行为。谋杀邓肯的罪恶感使得他们通过清洁自身来对抗道德焦虑,释放良心上的不安。因此,这也被后世心理学研究者称为“麦克白效应”[11]。对叛乱、谋逆、弑君行为惩罚的恐惧不安,与对滥杀无辜而产生的罪恶感,不断折磨着麦克白的精神,加重着他的病情。在登基为王后,出于对巩固王位与王权的担心,麦克白又杀了班柯。渐渐分不清现实与幻象区别的麦克白,又险些在宫宴上暴露他弑君的阴谋。麦克白的入侵性思维便是谋杀幻想,他认为身边的朝臣都是觊觎他王位的人。因此,他在杀害班柯后,变得嗜血滥杀。同时,在杀害邓肯、班柯后,麦克白与他妻子的关系也渐渐疏远,甚至在妻子病中,都不曾再见她。因为麦克白害怕面对他妻子,也即害怕面对自己所犯的可怕罪行,以免回忆起杀害邓肯、班柯的事实,唤醒自己内心的罪恶感与内疚感,想起自己曾经所犯的罪孽而惶恐不安。因为麦克白长期处在精神高度紧张的状态,陷入时刻对巩固王位的恐惧与不安中,变得多疑,草木皆兵,最终彻底成为了一位孤独的暴君。
对于麦克白来说,拥有一个能理解他,并与他精神高度契合的妻子是幸运,也是不幸。共犯是麦克白夫妇爱情的存在方式。预言,也成了他们必须要共同面对的诅咒,使他们共同承担着宿命带来的悲剧。
三、 成王败寇:悲观绝望的虚无主义
莎翁笔下的《麦克白》虽然是一部关于苏格兰王位及王权争夺的悲剧故事,但却隐喻着英格兰的王位之争。成王败寇,是历史的思维逻辑。历史通常由胜者书写,记录着被胜者的话语所建构的历史,而败者却失去了他们的话语权。因此,史书中败者常被塑造为丑恶、残暴的负面形象,以此来衬托胜者的英勇无畏,贤明伟大。
麦克白在英国历史中,也许曾是为带领苏格兰人民抗击过英格兰军队入侵的英雄帝王,但作为败者,被历史的胜者赋予了篡位暴君的身份。然而,历史的真相已是不可细细考证了。但仍可以面对苏格兰高地中仅存的废墟,对此做一大胆的猜想。在莎翁的多部作品中,时常会出现幽灵、鬼魂、巫术、魔法、女巫等等超自然因素,但这并不是一般写作意义上隐喻、象征与梦幻手法的运用,而是作为具有了英国历史文化传统与中世纪文化内涵的符号,有意识的出现在剧本的写作中的。在17世纪时,关于幽灵、女巫、魔法等异教色彩元素的描写,其实质是一种具有了政治涵义的语言表达符号。当时英格兰的统治权掌握在信奉新教的伊丽莎白一世女王手中,而拥护女王的朝臣,包括臣民,甚至女王本人都坚信着恶魔会以人的形象,混入人间,借助罗马教皇,或者一些反基督的异教徒,来推翻英格兰的新教政权。因此,《麦克白》中的女巫具有了象征和隐喻。她们不再只是一个超自然因素,而是作为一种时代文化的符号,出现在麦克白的世界,用预言的形式颠覆了苏格兰原本平和稳定的王权统治,建构了一个注定众叛亲离、一无所有的暴君,来亲手完成毁灭苏格兰的命运。对于这种历史惨状,恰好是伊丽莎白一世女王发自内心所深切忧虑与恐惧的。她担心自己受到未知的蛊惑,成为一个昏庸无能又骄奢淫逸的君王,从而将英格兰的未来与国家的命运葬送在自己手中。因此,终身未嫁任何人的伊丽莎白一世女王将自己嫁给了英格兰。
其实,莎翁笔下的麦克白与理查二世,虽不是同时代的君王,但在面对彻底的失败时所表现出来的情感与思想,却是极其相似的。麦克白在经历了战争的心理创伤后,又因为谋杀了邓肯、班柯,而逐渐失去了感知的能力,愈加变得恐惧不安,狂躁残暴,滥杀无辜。既容易受到惊吓,又容易生气暴躁。而情感上的麻痹与抽离感,也使他产生了一种世界是不真实的感受,使他最终陷入了对世界、对人生的虚无主义中。麦克白悲观而绝望地发出对得到王位,实现野心后人生的质疑与否定。在做出巨大的牺牲与付出后,所得到的却是“无味的渣滓”[12],是一场可怕的噩梦,除此之外,再无其他。麦克白夫人因此而精神崩溃,最终自杀。而麦克白自己却在失去生存的价值与意义后,苟延残喘,面对众叛亲离的下场,做着最后的困兽之斗。战死,也便成了他最后的愿望。如理查二世,在被自己的表弟亨利四世废黜后,囚禁在城堡的地穴中,除了死,便是直观地感受到生命的虚无与无意义。诚如麦克白所说“人生已经失去它的严肃的意义,一切都不过是儿戏。荣誉和美德已经死了,生命的美酒已经喝完,剩下来的只是一些无味的渣滓。”[13]的确,个体的生命在经历非常人的严酷考验与残酷打击后,是很容易产生悲观绝望的质疑的。接受命运的嘲弄,而活下去的人比起死去的人,却要面对着更多的未知风险。最终心力交瘁,不堪忍受。麦克白在得知妻子死后,发出了本剧最经典的一段独白,在这段独白中麦克白对生命的虚无与悲观情绪达到了顶峰。数百年后,在阅读到此段时,也依然能引起后世诸多虚无主义者情感与思想的共鸣。“明天,明天,再一个明天,一天接着一天的蹑步前进,直到最后一秒钟的时间。我们所有的昨天,不过替傻子们照亮了到死亡的土壤中去的路。熄灭了吧,熄灭了吧。短促的烛光!人生不过是一个行走的影子,一个在舞台上指手划脚的拙劣的伶人,登场片刻,就在无声无息中悄然退下;它是一个愚人所讲的故事,充满着喧哗与骚动,却找不到一点意义。”[14]麦克白与理查二世所展现的正是人类共同的人性。临死之时,却终究得不到诗意的慰藉与灵魂的疗救,在孤立无援的处境中,孤独地陷入虚无主义的黑暗深渊,留下一幕幕悲观绝望又十分深刻的人生思考。虚无主义是莎翁作品中一个永恒的情感体验与思想主题,在《哈姆雷特》《理查二世》等作品中,也都有所体现。莎翁的剧作已不单纯只是一部部用来表演娱乐的工具,而是通过他的每一部剧作,每一个人物,来传达出他对人生、对世界的看法与认识,尤其是表达着他对人类共同情感与人性的关注、思考。莎翁将人类情感与人性中最核心、最普遍的价值呈现出来,以启发人的思考,并最终达到净化人心的目的。
《麦克白》是莎翁笔下最黑暗的剧作。莎翁用他的剧作书写着人心的阴暗,挖掘着人在极端的心理处境中种种的困兽之感。人的本性,在西方基督教看来是邪恶的,是有着不可宽恕的原罪,与被引诱而作恶的无限可能。而正是莎翁笔下所有作品的不确定性与模糊性,才使得《麦克白》这部经典的不朽剧作,交由演员与观众去思考,去发现,最终演绎出多种多样的版本。经由历史的发展,不断地丰富着剧作的思想内涵,衍生出无限阐发的可能性,始终不断地在赋予着剧作中的人物,以鲜活的生命力与时代气息。而这也正是莎翁剧作成为人类的文化宝藏,经久不衰的魅力所在。
【参考文献】
[1]Curt R.Bartol,Anne M.Bratol[美].犯罪心理学,第七版[M].杨波,李林等译. 北京: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15.
[2]Jerry M.Burger[美].人格心理学,第八版[M].陈会昌译.北京: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14.
[3]弗洛伊德[奥].自我与本我[M].林尘,张唤民,陈伟奇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5.
[4]弗洛伊德[奥].精神分析引论[M].高觉敷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
[5]莎士比亚[英].莎士比亚全集·悲剧卷,下[M]朱生豪译.南京:译林出版社.1999.
[6]钱乘旦,许杰明.英国通史[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2012.
[7]Oryx-Z.PTSD:魔鬼从未离去[N].果壳.2015.12.29
[8]亵渎电影.电影麦克白影评[N].奇遇电影字幕组.2016.1.24
 最新评论
最新评论|
版权所有© 中外文学研究课题组 |